|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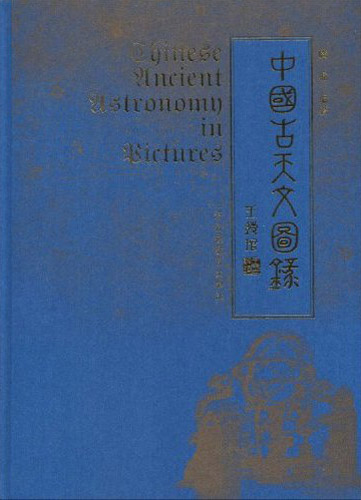 前段时间笔者参加了两次小型学术活动。一次是参加法国国家科学中心数学史教授林力娜(Kerine Chemla)被聘为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的受聘仪式。在仪式完成后林力娜教授为与会师生作的一场题为《中国数学史上的视觉辅助用具——汉代至宋、元》的报告,对图形在中国古代数学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另一次是参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博士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一位学生报告了他准备的题目是《视觉科学编史学:科学编史学视角下的视觉表现研究》。一时给我的感觉是,无论是卓然成名的大师专家,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都对科学史研究中图像的重要性开始关注起来了。 前段时间笔者参加了两次小型学术活动。一次是参加法国国家科学中心数学史教授林力娜(Kerine Chemla)被聘为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的受聘仪式。在仪式完成后林力娜教授为与会师生作的一场题为《中国数学史上的视觉辅助用具——汉代至宋、元》的报告,对图形在中国古代数学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另一次是参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博士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一位学生报告了他准备的题目是《视觉科学编史学:科学编史学视角下的视觉表现研究》。一时给我的感觉是,无论是卓然成名的大师专家,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都对科学史研究中图像的重要性开始关注起来了。
几乎同时,我又收到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寄来的一册潘鼐先生编著的《中国古天文图录》,翻阅之下,觉得这部书无论是在强调天文学史研究中图像之重要性的一阶研究方面,还是在视觉科学编史学的二阶研究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图像所传递的信息,是文字无法取代的;反之,文字所表达的意思,有时也是图像所无法胜任的,所以图和文经常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汉语中就有图书、图籍这样的词汇。然而,也许是由于印刷技术上的原因,或者其他什么因素的作用,总起来看,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出版物中,文字是战胜了图像的。例如1788年拉格朗日出版的《分析力学》,也许是为了展示数学分析的力量,全书没有使用一幅插图。电视这种大众传媒形式的兴起,被一些人看做是开启了图像战胜文字的时代。近来大量图文书的出版似乎是呼应了这一潮流,其中不乏学术书籍。
小到天文学史这么一个很专门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也有以图像为主题的书籍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和陈美东主编的《中国古星图》等。从书名上可知,前者主要关注的是天文文物,后者则是着重研究中国古星图,而潘鼐先生的《中国古天文图录》收录的古天文图像所涵盖的范围则要广得多。
《中国古天文图录》全书一共分为8篇,第1编收录了“上古时期——新石器时代至两晋时期”的天文图像。第2篇收录“中古初期——南北朝至五代十国”的天文图像,其中的亮点为敦煌石窟中的天文书籍和图像,以及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国所产生影响的星神画像和佛经中的天文图像。第3篇收录“中古中期——宋辽金元时期”的天文图像,第4篇收录“中古后期——明代”的天文图像,第5篇为“近世时期——清代天文星象图”。第6篇为“近世时期——清代天文仪器图”,第7篇“朝鲜与日本的中国天文图”收录了流传于朝鲜和日本的中国古星图和天象图等。第8篇为“星名中西对应恒星图表”。此外,该书在最后还作为附录收录了32套较为完整的出自历代古籍中的天文图像,占到全书篇幅的1/3左右,是对正文的重要补充。
据笔者统计,《中国古天文图录》一共收录天文图像339项,有时一项包含多幅图片,全书图片数量超过1000幅,是迄今所见收录最全面的图说天文学史专著。这样一部著作的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该书对于一阶意义上的天文学史研究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作者穷数十年心力收集的这些天文图片,大大方便了读者对天文学史的学习和了解。在讨论到古代的星图或仪器时,观看一幅直观的古代星图或仪器图片能获得千言万语所达不到的学习效果。即便在学术层面上,该书也大有裨益。譬如笔者在看到图2.14“释典天文图像”中收录的一幅《火罗图》(38页)时,留意到该图对计都星的描述与佛经《梵天火罗九曜》中的对应描述有异——一般认为《火罗图》是对《梵天火罗九曜》图文化的结果,对后者笔者已有专文考证。《梵天火罗九曜》中记载:“蚀神头从正月至年终常居此二宿:翼、张;蚀神尾从正月至年终常居此二宿:尾、氐。”而《火罗图》中蚀神尾“从正月至年终常居”的宿变成了“危、室”二宿。这一差异可能暗示着作为蚀神首尾的罗睺、计都两曜的天文含义发生变迁的线索,值得深入研究。其次,《中国古天文图录》对作为二阶研究的“视觉科学编史学”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实例。书中所采用的大量来自古代文献的天文图像,本身就说明了科学史文献中图像的重要作用和悠久历史。
该书作者潘鼐先生是天文学史界的前辈。17年前,笔者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便结识了潘先生,此后多有请益。潘先生治学的勤奋和对天文学史的热情,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80多岁高龄、双目视力衰退、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他仍然笔耕不辍。一次我劝潘先生应该保重身体,可以颐养天年了。潘先生说等完成三件事情后,他就可以休息了。这三件事是:修订并再版《中国恒星观测史》、汇编出版《崇祯历书》、编著出版《中国古天文图录》。如今这三件事情都已经顺利完成,我真心地为他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