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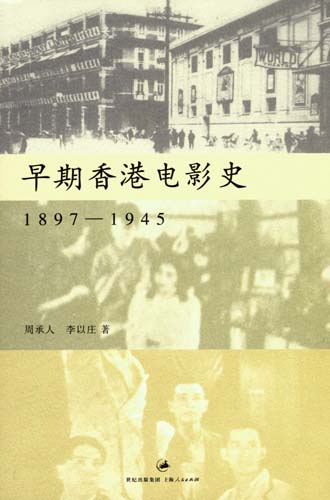 去年秋季到深圳参加读书月三十本好书评选,得识马家辉先生,彼时他蓄浓髭,为陈子善笑称“青年马克思”。一日饭后在酒店房间闲聊,他取出刚在上海书店出版的精装小册《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相赠,是他谈电影的集子,此前我曾有北京三联书店版《目迷·耽美 卷一 江湖有事》与《卷二 爱恋无声》二书,读后颇喜欢他写电影的那些文字。隔日去香港,于书店寻得他早期几册港版小册子,写井市时尚,与他写电影大有距离。今年又得三联书店寄来新书《死在这里也不错》,为其游记结集,可知他写作多近于现代生活,又带有“废墟里看见罗马”式的怀旧情绪,撩起人们心底的温情。他写游记与写电影随笔皆好,难怪林青霞会给他的书写序,而他旅游又不忘观赏当地电影,大有时空叠替之感。借此话题说开去,写电影文章大体可分作两类,一是谈电影观赏,一是谈电影艺术技巧,法国人安德列·巴赞著有《电影是什么》,则观赏与艺术兼论。这之外另还有一种谈电影旧事的文字,按时间线索写来,成为电影发展史。 去年秋季到深圳参加读书月三十本好书评选,得识马家辉先生,彼时他蓄浓髭,为陈子善笑称“青年马克思”。一日饭后在酒店房间闲聊,他取出刚在上海书店出版的精装小册《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相赠,是他谈电影的集子,此前我曾有北京三联书店版《目迷·耽美 卷一 江湖有事》与《卷二 爱恋无声》二书,读后颇喜欢他写电影的那些文字。隔日去香港,于书店寻得他早期几册港版小册子,写井市时尚,与他写电影大有距离。今年又得三联书店寄来新书《死在这里也不错》,为其游记结集,可知他写作多近于现代生活,又带有“废墟里看见罗马”式的怀旧情绪,撩起人们心底的温情。他写游记与写电影随笔皆好,难怪林青霞会给他的书写序,而他旅游又不忘观赏当地电影,大有时空叠替之感。借此话题说开去,写电影文章大体可分作两类,一是谈电影观赏,一是谈电影艺术技巧,法国人安德列·巴赞著有《电影是什么》,则观赏与艺术兼论。这之外另还有一种谈电影旧事的文字,按时间线索写来,成为电影发展史。
《香港早期电影史》以香港一地记述其电影历史,时间在1897到1945约五十年,此类地域文化发展历程,在早期颇为显著,尤以上海电影堪作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代表,然电影这门艺术在中国很受政治影响,1949年后中国内地电影呈北京与上海并立景况,而至今日,则转变为以北京为中心。但香港电影偏于一隅,受殖民化影响甚重,又有岭南热带风情习俗及语言之异,风格自别于内地,可独立成篇章。作者周承人、李以庄二人在书前《自序》言1981年即有“香港电影研究”之意,至1984年始得着手开展,可见作者研究香港电影迄今已二十多年,成此书颇不容易。书中所论香港电影发展颇多琐碎,是以细节连贯成脉络,串而为史,因此读来饶有趣味。不过作者在《自序》里列出四条:“我们根据史实在以下问题取得若干较大突破1.确定了电影传入香港的时间;2.解读黎民伟的《自述》,确证华美公司是美国人布拉斯基独资开办,从而对一系列问题重新认识;3.梳理史实,确认黎北海对早期香港电影作出的贡献,证明他才是‘香港电影第一Take’;4.深入研究了港/沪联华影业公司,重新确定罗明佑在中国电影/香港电影中的历史地位。”,并言:“这些都是我们奉献给读者的研究成果”,很有点自我鉴定的味道,只是不曾想到读者未必认同,反倒使读者看出作者认知水平,免不了以自身立场对电影艺术作好与坏的判别,譬如对鸳鸯蝴蝶派的排斥等。其实早期中国电影当以鸳鸯蝴蝶派故事为主,渐渐转移为鸳蝴派与新文学并立而发展成为现实主义流派,大不必一味抹杀掉。
是书分五章组成,另附《香港电影大事记(1897—1945)》,其第一章《香港电影的缘起》中有《电影何时传入香港》一节至为重要,颇多史料整理和考据。第四章《抗战期间的香港电影1937—1941》与第五章《沦陷期间的香港电影1941—1945》尤多论述,此时期对香港电影的发展影响甚大,上海文化界人士离沪赴港使香港文化得到新的艺术感受。由沪来港的报纸与文学杂志铺垫出上海与香港同步发展的景象,也使香港成为上海文化的后方。作者因此所述:“战时内地文化精英到香港,带动香港抗战文化事业的繁荣,香港电影从进步文学方面得到支持,亦有助于提高香港电影素质。香港电影界中粗制滥造、思想意识低下的纯商业路线,遭到激烈的批判。”则未免想当然,毕竟纯商业电影未必粗制滥造,更不可与“思想意识低下”划在一起,可知作者对香港电影研究有成,论述则不甚高明。
其实写这类地域电影史,还是应以当地作者来作研究为好,尤其香港一地,生活与思维方式皆别于内地,说来大陆与台湾文化趋于相同,惟香港区别甚大。前面说到马家辉先生谈电影的文章,很可看出香港人的生活态度与赏识趣味,可举香港警匪片与黑社会打斗片,近似好莱坞的作风,都为大陆与台湾所不可复制。以此而言,写香港电影史当以熟知香港社会与生活为要,作者身在广州研究香港本无不妥,然以内地思维推论香港,则印证作者自我所言“隔山买牛”,陷于立场辩白与政治说教,使好作品白璧微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