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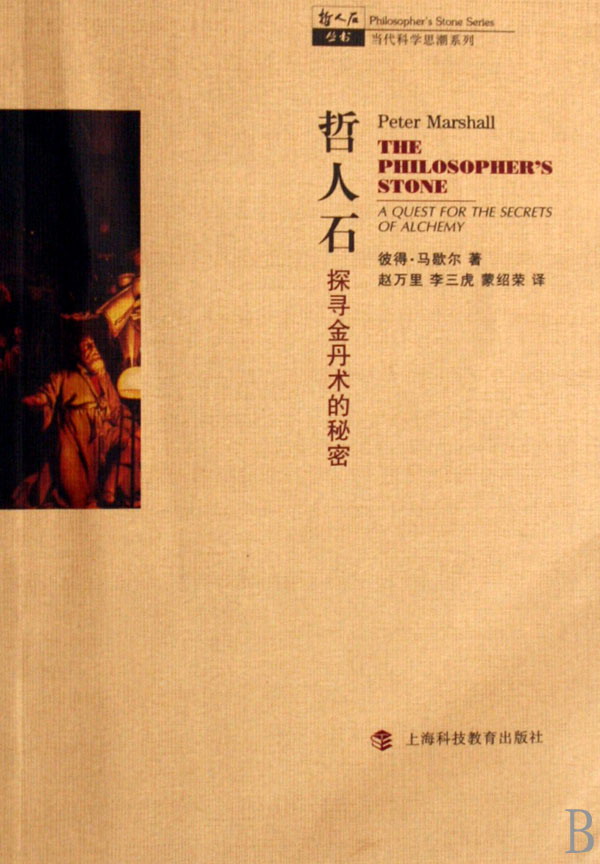 国内喜欢读点科普书的人,恐怕很少有从未接触过“哲人石丛书”的。这套书从1998年底开始出版,迄今已有10个年头。10年间,它出版了85个品种,其中不乏《确定性的终结》、《美丽心灵》、《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等一印再印的畅销书、常销书。在“谷歌”上输入“哲人石丛书”5个字,可得到26万9千余条检索结果,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国内喜欢读点科普书的人,恐怕很少有从未接触过“哲人石丛书”的。这套书从1998年底开始出版,迄今已有10个年头。10年间,它出版了85个品种,其中不乏《确定性的终结》、《美丽心灵》、《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等一印再印的畅销书、常销书。在“谷歌”上输入“哲人石丛书”5个字,可得到26万9千余条检索结果,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科普图书引进出版热潮中,“哲人石丛书”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此前有名气甚大的“第一推动丛书”、“科学大师佳作系列”,同时期有“支点丛书”、“三思文库”,此后则有“新视野丛书”、“盗火者译丛”等。这些丛书在最初出版时都曾轰轰烈烈,但大多倏忽而逝,能够坚持10年以上的,唯有湖南科技出版社的“第一推动丛书”和上海科教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若论出版规模,后者又远超前者。正像清华大学教授刘兵所说:“这样的出版努力,肯定是会在中国当代科普图书出版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的。”
追溯“哲人石丛书”出版的过程,就不能不提到这套书的两位策划人——潘涛和卞毓麟,也不能不提到10年来上海科教出版社的相关领导。
“1997年4月13日,我第一次见到了当时任出版社总编辑的翁经义老师。翁老师请著名科普作家李元、郭正谊等先生在北大小南门对面的烤鸭店里吃饭,我也在座。饭桌上,翁老师谈起引进优秀外版科普图书的构想,那份豪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潘涛回忆说。那时,潘涛还在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读博士。
1997年,卞毓麟也还在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现国家天文台)搞科研。由于热心科普,他也成了翁经义频频光顾的对象。“翁老师说:‘我们先做30种书,大不了赔250万,我们做好了这个思想准备。’这个表态,让我对这个项目充满了信心。”卞毓麟回忆说。
这样谈来谈去,潘涛、卞毓麟和出版社越走越近,最终的结果是,一年后,卞毓麟、潘涛都成了上海科教出版社的编辑。
“为引进我们两人,出版社在住房、待遇等方面都是特事特办。现在想来,出版社是有点冒险的,毕竟,那时候我们俩都还从来没有真正做过图书编辑呢。”潘涛告诉记者。
实际上,选择加盟出版社,潘涛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而卞毓麟则中断了科研生涯,老伴也不得不提前退休。“有朋友为我惋惜,觉得在科研机构的社会地位要远远高于出版社编辑,而且有更多时间搞科普创作。我回答说,自己写科普,每年最多写一两本,而做编辑,每年至少可以编七八本非常优秀的科普书出来。后一种选择对科普事业的贡献当然更大,这是我所看重的。”卞毓麟说。
上海科教出版社为了一个出版项目,同时引进一位研究员、一位博士,如此大动作,亦在出版界传为佳话。
对于一套大型丛书,起一个响亮的名字非常重要,这套书为什么会起名“哲人石”呢?
潘涛回忆说:“最早的时候,我们曾想仿照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命名为‘汉译科普名著丛书’,但后来觉得,还是要另起一个更有特色的名字。记得那时我还在学校,翁老师打长途电话过来,我跑到传达室去接,他问起我,我脱口而出的就是‘哲人石’这三个字。出版社研究一番之后,就以此向上面报了选题。”
潘涛说,从字面意义上讲,“哲人石”有哲人的他山之石之意,更重要的,这个词在西方科学史、文化史上的意蕴极为丰富。
《辞海》对“哲人之石”的解释是:“中世纪欧洲炼金术士幻想通过炼制得到的一种奇石。据说能医病延年,提精养神,并用以制作长生不老之药。还可用来触发各种物质变化,点石成金,故又译‘点金石’。”炼金术、炼丹术(统称“金丹术”)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有悠久传统,现代化学正是从这一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哲人石”这个词与科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古人的理解则更为“玄乎”:“哲人石”象征了最高的物质性和最高的精神性。以“哲人石”冠名,就隐喻了科学是人类的一种终极性追求,也赋予了这套书以更多的人文内涵。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注意到,“哲人石丛书”近年接连推出了《寻求哲人石——炼金术文化史》、《哲人石——探寻金丹术的秘密》等两本书,颇有点题之妙。
“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哈利·波特》的第一部是《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所谓‘魔法石’,其实就是‘哲人石(Philosoper’s Stone)’的一种通俗译法。”潘涛告诉记者。
取名“哲人石”,也预示着这套书将不限于传统的知识科普。正像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所说,“书中所谈,除了科学技术本身,更多的是与此有关的思想、哲学、历史、艺术,乃至对科学技术的反思。这种内涵更广、层次更高的作品,以‘科学文化’称之,无疑是最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