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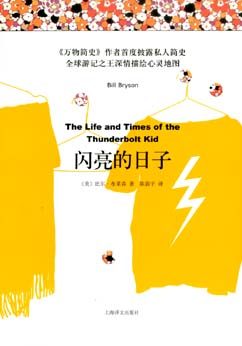 也许当成年已久的某一刻,你才会顿悟,童年正是成人时代的一场前戏:摸索,探入,爬上去又掉下来。 也许当成年已久的某一刻,你才会顿悟,童年正是成人时代的一场前戏:摸索,探入,爬上去又掉下来。
社会是按成人的尺寸来设计的,比一人高一头的门,长出一小截的床,能探出上半身的窗,都遵循能带来最大安全感的比例。然而大人的本能里也许存着个“一夜变小”的梦。
裹在襁褓里的人做什么都是探险,因为世界不在他/ 她的掌控之下,格林童话里老写到大拇指、巨人国之类的故事,智勇双全的正常人一再对巨人实施成功的戏耍与偷袭,满足孩子挑战成人世界的快意。另一个例子是米歇尔·图尔尼埃的小说,他在《阿芒迪娜与两个花园》中写到那个追随着小猫咪爬上院墙的小女孩,她只是朦胧地想看隔壁的另一个花园的样子,这表达了一种更带女性味道的冒险冲动。在动画片里我们常常看见树屋,那里面空空如也,没有空调、烤箱、高尔夫球具和商务管家,它的建造者们甚至不懂什么叫回归自然,只是想离开地面,也离开成人的视线,去做一些集体性的、秘密的事情。
我羡慕有树屋的孩子,哪怕比尔·布莱森和他的26个男同学当年把它用作性游戏的场所。看那些教育学家谆谆教诲说儿童的模仿本能很强,家长要注意言行,懂得身教,我就想孩子若有自由,何至于给家长添这么多负累。布莱森12岁就知道翻家里的《花花公子》看,也没妨碍他后来当上世界级专栏作家。
要说不眼红布莱森是假的,这个爱翻故纸堆的大胡子,从不忌惮因显摆他作为孩子所享有过的自由而遭人嫉妒,就连在感伤怀旧于那些已不存的景观——大片农场、小商铺、汽水屋,这些东西让我想起集体合作社时期的中国,貌似那里一度也洋溢着“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人才拥有的乐观主义”——的时候,仍可通过文字看见他嘴角余波未消的笑纹。这种自由的泉源,在《闪亮的日子》每章开头精心选登的报纸旧闻中露出端倪,那就是对猎奇心理的普遍纵容,政府和社会不但尊重公民的知情权,甚至把后者当成求知欲旺盛的孩子。1957年9月20日《得梅因纪事报》载:“波科多宝格湖搜索落水者的行动于本周二被取消。原因是自愿协助搜索者中现年23岁、来自东汉普顿的罗伯特·豪斯曼就是被搜索者本人。”没加一句破坏气氛的道德判断,也没社会学家出来分析肇事者的家庭背景。
可怕的是大人们大都已无从体会孩子涉险的愉悦,反而粗暴地把他们从椅背上捉下来放稳。太多的人一笔勾销了自己的童年(最多例行公事地留几本影集),不能主动理解孩子式的对制造自得其乐的惊奇的需要:在我掰开平生拿到的第一片夹心饼干,舔掉一圈奶油,再蘸着牛奶咀嚼剩下的干货时,我以为我是史上第一个发明这种能带来开箱取宝式快感的吃法的人;我把路上捡到的半个铃铛盖带到学校,天天摩挲着给人看,声称是银器;初中时我旷课跑20里地去地摊上买山东菏泽出的世界名画扑克牌,我坚信发现世界名画里的裸体女人并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人,数我为先行者。
比尔·布莱森在过了三分之一篇幅的地方开始了第六章:“性及其他娱乐”。在此之前,我已经知道他像我一样一条一条地把油纸从警棍一样坚硬的冰棍上撕下来,并屡教不改地让舌头同它死死粘在一起;在此之后,性启蒙成为所有回忆的主线。自从偷看到父母床戏的那一天开始,我们亲爱的布莱森同志就再也没有放弃过对女人肉体的幻想,但他不用对着一副套色不准的劣质扑克牌发呆,而是直接找画报,造树屋,并不遗余力地引诱女孩子到那里去。
在崇仰“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地方,自由原则上普适于每个人,而在电影等级、烟酒销售和娱乐场所准入等特定环节进行适当把控。青春期的冒险终究是任何人不能剥夺的特权。布莱森曾被州立博览会的脱衣舞场挡了驾,这个州的立法一再提高性表演场所的准入年龄门槛。在满14周岁那年,布莱森带齐了所有证件,先在博览会大厅里事无巨细地参观了一大圈,为的是美美地享受那一刻。这个露天市场展出来自这个农业大州各个角落的产品,棉被、玉米、果酱、生猪、黄油做的奶牛,等等,于是他说:“可能这是史上第一次有人把棉被和奶牛当成前戏……”
我似乎顿悟到,童年正是成人时代的一场前戏:摸索,探入,爬上去又掉下来,为了美美地享受即将到来的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