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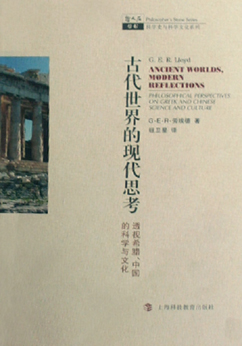 □江晓原 ■刘 兵 □江晓原 ■刘 兵
□劳埃德这本书,论题很宏大,态度很严肃,以至于我觉得需要以一段八卦来开始我们的对谈了。
你肯定还记得,大约两年前,我们一群朋友在电子邮件中为“科学”的定义应该取窄还是取宽爆发了争论,两派互不相让,最终也没有达成一致,真正是“君子和而不同”了。这场争论在我们圈子里留下了“宽面条”和“窄面条”的典故,时常被人引用。在争论中,你是坚定的“宽面条”派,而我和钮卫星都属于“窄面条”派。
有些反讽的是,后来钮卫星承担了劳埃德书的翻译任务,而他发现,劳埃德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宽面条”派,出现了“窄面条翻译宽面条”的有趣局面。
劳埃德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些演讲稿的集结,不过劳埃德当然修订了这些讲稿,并细心将它们“焊接”起来,而且在起承转合之际尽量做到“平滑过渡”。
由于上面这个原因,本书的主题就不可能不宏大了。说实话,这么宏大而宽泛的主题,也就是劳埃德这种德高望重功成名就的人(已因“对思想史的贡献”而被英国女王封赐为爵士),去尝试玩一把还差不多,别的学者多半会望而生畏。
■你提到了此书的译者,“窄面条”钮卫星教授。我觉得,他在为此书所写的译者序,对全书重要观点的梳理很全面,是对此书很好的总结。
无论是通过详细地阅读全书,还是仅仅简要地浏览一下译者序,读者都会发现,其实此书与其说是历史考察,倒不如说是历史反思。因为此书有很强的理论色彩,也很有科学编史学的意味。例如,像作者在开篇就探讨的对于一个古代社会,我们怎么才能够去理解,又能获得多大程度上的理解的问题,以及像古代世界有没有科学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你和钮卫星将他归入“宽面条”派),形式逻辑和它的规则在多大程度上或在什么意义上是普遍有效的?关于真理和信仰及其与跨文化之关系等。这些问题几乎都是典型的编史学问题。也就是说,劳埃德是在对古代历史长期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一些历史研究中关键性的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并给出回答。
□你看到此书的科学编史学意义,倒是别具只眼,这当然和你长期关注科学编史学问题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我非常赞成。你对钮卫星译者序的评论,也非常准确。
在第二章“古代文明中的科学?”中,劳埃德相当深入地讨论了应该如何定义“科学”这个问题。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将“科学”与“正确”的关系引入了这个问题。因为古代文明中的许多知识和对自然界的解释,在今天看来都已不再“正确”了,这成为那些认为古代文明中没有科学的人所持的重要理由。但是劳埃德指出:“科学几乎不可能从其结果的正确性来界定,因为这些结果总是处于被修改的境地”,所以他认为,“我们应该从科学要达到的目标或目的来描绘科学”。这一点实际上是科学史中的基本常识。
那么什么才算是“科学”的目标呢?这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定义问题。劳埃德的定义是:“理解客观的非社会性的现象——自然世界的现象”。也就是说,抱有上述目标的活动和成果,都可以被视为科学。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宽泛的定义!按照这样的定义,任何有一定发达程度的古代文明,其中都会有科学。看看,劳氏的科学面条,可谓宽矣!
■其实,这涉及到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观”,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人类认识自然的知识。劳氏长期以来专攻古希腊研究,一方面,这样的研究通常是在与近现代科学相关的意义上展开;另一方面,如果真正深入到历史中,古希腊的“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之差异,也会被明显地注意到。只是长期以来,人们过多地关注前一方面,而后一方面,却是要真正有历史感和历史悟性的人,才会注意到并有所发挥。劳氏在此基础上又把中国古代科学拉进来进行比较,就更有意思了。
说到任何有一定发达程度的古代文明,其中都会有科学,这样的观念已被西方当下一些基础教育改革理念所采纳(我国基础教育中的科学观却大不一样)。难得的是,像劳埃德这样的老一辈的学者,也能够有如此开明的见解。
以往在我们关于“宽”、“窄”面条之争时,双方其实都只是在命名和逻辑的意义上采取不同的定义,而在对人类知识的多样性,“窄”科学之局限性等方面,并无太大分歧。但尽管如此,看到劳氏的“宽面条”,我还是倍感高兴。
□其实不是“并无太大分歧”,而是几乎就没有分歧。我们的科学定义“宽窄之争”实际上只是技术或策略层面的不同,相关的目标和基本价值观念是一样的。所以看到劳氏有如此开明的见解,我们不仅应该“倍感高兴”,同时还应该由此看到,国内学术界在如何看待科学技术这样的问题上,仍然相当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