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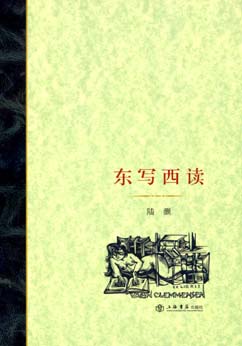 “东写西读”,也是“东拼西凑”。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掌故,陆灏左右逢源,信手拈来。他读了很多书,这些书不拘一格,无奇不有。我不清楚此公平时有没有做笔记的习惯,据他所说:“这种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问题的读书方式,虽然在正宗的历史学家看来,只是文人们地地道道的浅见薄识,但对我这样的读书只求趣味不为写论文的人来说,几乎就是全部的兴趣所在。”一般是不会和做学问一样老实记笔记的。这种贪玩的读书心态,多是把好玩的事随便扔进脑子里,现用现取或是用时再找出处去核实。这种记忆力让人羡慕。 “东写西读”,也是“东拼西凑”。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掌故,陆灏左右逢源,信手拈来。他读了很多书,这些书不拘一格,无奇不有。我不清楚此公平时有没有做笔记的习惯,据他所说:“这种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问题的读书方式,虽然在正宗的历史学家看来,只是文人们地地道道的浅见薄识,但对我这样的读书只求趣味不为写论文的人来说,几乎就是全部的兴趣所在。”一般是不会和做学问一样老实记笔记的。这种贪玩的读书心态,多是把好玩的事随便扔进脑子里,现用现取或是用时再找出处去核实。这种记忆力让人羡慕。
陆灏的选材和加工技术堪称一流。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的故事,被揉团拉扯几下,一眉一目、一手一脚地就出了模样。举个例子,《笺注》一文中有一则文章《一树梨花压海棠》,写了很小的一件事,考证“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出处。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诗出自苏东坡,但陆灏考证的过程,读来却饶有趣味。
起因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陆灏说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调调,这种书读了不舒服。他用朋友吴劳的话为这类书定了性:每个老头心中都有一个洛丽塔。根据小说《洛丽塔》改编的电影名为《一树梨花压海棠》,陆灏对这个译名很是佩服,由此开始了对这句诗出处的考证。袁枚70岁写的《不染须》里,有这句诗;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记过这么一段话;最后,在苏东坡那里找到了一半答案。苏东坡的朋友张先80岁时娶了一个18岁的女孩为妾,得意地赋诗一首:“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苏东坡作诗调侃道:“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装。鸳鸯被里成双对,一树梨花压海棠。”这诗出自哪本典籍,没有找到。
其文最妙的是结尾。杨振宁偕新婚妻子到北京,当年西南联大的同学许渊冲请杨氏夫妇吃饭,让学生在饭桌上读这首诗,一面还详为解释,杨听了哈哈大笑。
“一树梨花压海棠”这句诗用作《洛丽塔》的译名,早有耳闻,但认为很值得商榷。此译斯文是斯文了,雅致是雅致了,文化上的误读也随之而来。虽说故事是那样的故事,但诗中体现的士大夫风流自赏的文化格调,与小说所表达的还是大相径庭。过于调侃把玩,而沉重压抑少了。正如学者王怡说的:“一句淡淡的东方雅词,足以让莎士比亚变成一段红楼梦。”
陆灏之意不在中西文化的对比,而在围绕一句诗展开的中西古今的一连串故事。陆灏的故事讲得极好,而且是只讲故事,不谈道理。把故事讲好了,至于道理什么的,诸君自便吧。
陆灏这种大谈掌故的读书方式,不是人人都适合的。掌故这类东西,不是新闻,好不好,不仅要看内容和讲的技巧,更要品味道,一路经风沐雨的陈香。这味道来自掌故本身,也来自讲故事的人。同样的掌故不同人讲,味道大不相同。听掌故是听故事,讲故事人的阅历和道理都藏在了故事里。沧桑不言,风雨无声。少了这种经历阅历,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剩下的,就只有故事壳子。简单的“抄书公”就不让人佩服了。
叶灵凤有一篇叫《作家和友情》的文章,讲了“两明一暗”三个故事。两个明说的故事,一个是都德在他的《巴黎三十年》的回忆录中记录的和屠格涅夫的交往。屠格涅夫侨居巴黎,都德、左拉、佛洛贝尔等人常与之聚会。大家谈论文艺、人生和家庭,气氛融洽,感情和睦,相处很是不错。屠格涅夫去世后,都德从屠格涅夫当时给朋友的信中得知,屠格涅夫根本瞧不起他,说他是“我们同业中最低能的一个”。都德很伤心。
另一个故事写的是神秘的“龚果尔笔记”。法国的龚果尔兄弟用毕生心血记叙了他们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和政治人物。这些日记只发表了9卷,其余未发表的,根据大龚果尔于1896年临去世时遗嘱,要在他去世20年以后才可发表。这些日记由龚果尔学院封存着,到了1916年,遗嘱上规定的20年期限到期之时,学院推举了两位代表审查这些日记是否可以发表。这两位代表回来后噤若寒蝉,只是摇头说:“为了免除诉讼、暗杀、自尽,以及社会上其它的不安起见,这日记最好要再隔上一世纪始能发表。”日记的内容如何,从这情形上就可想而知了。
一个暗写的事件是关于鲁迅的。文末,叶灵凤说:“我相信,鲁迅的日记如果一旦一字不改被发表起来,那些自命为鲁迅的朋友们更不知要如何的伤心了。”
前面的两个故事有趣,但是,如果你了解发生在鲁迅和叶灵凤之间的纠葛,就会明白,明说的故事不过是醉翁之意,最后这看似不经意的寥寥数笔,才是令人回味无尽的关键所在。
最后要说一句,叶灵凤是说自己的事,陆灏的“一树梨花压海棠”是别人的事。也许是还不老,此事尚未引起他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