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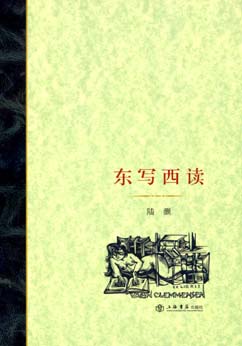 今年44岁的陆灏,曾编辑《万象》杂志多年,史海钩沉,中西求索,在报纸和周刊的薄弱环节,补一些读书人消遣的“甜俗”趣料,其书卷气和对现实的入微体贴至今让人回味;他参与编辑的一套丛书,题目就叫“书趣文丛”,强调书的趣味,强调好书的“事”、“识”、“情”;他自己撰写《东写西读》一书,收录他近年杂览闲读所写的文史小品,往往是一段掌故,一点趣味,几分才情,几段妙论,仿佛餐后甜点,独具品位和生趣。他不论读书、写书,还是编书、编杂志,都一脉相承地经营着他的个人阅读趣味,体验读书的私秘乐趣,从不旁骛。 今年44岁的陆灏,曾编辑《万象》杂志多年,史海钩沉,中西求索,在报纸和周刊的薄弱环节,补一些读书人消遣的“甜俗”趣料,其书卷气和对现实的入微体贴至今让人回味;他参与编辑的一套丛书,题目就叫“书趣文丛”,强调书的趣味,强调好书的“事”、“识”、“情”;他自己撰写《东写西读》一书,收录他近年杂览闲读所写的文史小品,往往是一段掌故,一点趣味,几分才情,几段妙论,仿佛餐后甜点,独具品位和生趣。他不论读书、写书,还是编书、编杂志,都一脉相承地经营着他的个人阅读趣味,体验读书的私秘乐趣,从不旁骛。
与记者说到书,说到阅读,陆灏随和、亲切,滔滔不绝,与起初不愿接受采访时的疏远简直判若两人。他盛赞深圳读书月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来,买书的人多了,读书的人多了,深圳的文化氛围更浓了。他希望深圳的报纸阅读版面能热中求冷,在报道某一本或几本热销书的同时,能推扬一些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在读者中培养对书的爱好和兴趣,养成读书的习惯。他希望更多的人和他一样享受阅读的乐趣。
读书只求趣味
陆灏说,他特别幸运的是,从小到大没人逼他读书,更没有谁逼他读不喜欢的书,换句话说,他没有读“伤”过。读书是他的自觉自愿,是充满快乐和趣味的过程。小时候,是一个书荒的年代,能读的书很少,好不容易得到一本好书,也得限时限刻读完。他记得有一次家里借到一本当时很难得到的《基督山恩仇记》,他与父母同时看,一个通宵读完,第二天又转到阿姨、舅舅手里。那时,陆灏最爱读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前者家里藏着一本老版本,后者借“评《水浒》运动”而开禁。后来他读了《西游记》、《说岳全传》、《三侠五义》等古典小说。学校也没有逼着他读什么,他可以按照兴趣读自己喜欢的书。大学学的是新闻,更有时间自由阅读。这个时期他几乎什么书都读,兴趣很广,侧重点则在外国文学和哲学。工作后也没有为写论文、评职称而功利地读书。在他写的《东写西读》后记里,他说:“读书是我的一项爱好,对我来说,除了消遣取乐,读书并没有其他功效,既不为考试,不为研究,也不是为了写书评。”这种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问题的读书方式,可能在有的人看来,会认为是文人地地道道的浅见薄识,但对陆灏这样读书只求趣味不为功利的人来说,其实就是全部的兴趣所在。尽管如此,陆灏认为为功利读书也没什么不好,毕竟考学、升职、研究,也都是必须的,但这样的读书可能乐趣少些,以前说的“十年寒窗苦”,肯定是指功利性读书,但为消遣而读书,何苦之有?
读书不跟风
记者要陆灏给读者推荐一本2007年度最值得一读的书,这使他非常为难。他说每个人的阅读兴趣不同,他认为最好的未必是读者也认为最好的。陆灏说他读书很随兴,随自己的兴,不跟风,即使所有人都在谈论某一本书,如果他没兴趣,照样不读。陆灏喜欢从别人的著作中寻找书目线索,然后找来读。作家阿城曾写过一本《威尼斯日记》,里面引用了不少《教坊记》里的有趣故事。陆灏因此费了好些功夫,终于找到了《教坊记》,却发现原来书很薄,精彩的故事都被阿城引用,实在是不经读。多年前,陆灏曾发下“宏愿”,要把钱锺书《管锥编》中提及的英文书全部找来读一遍,并为此抄录了一份洋洋大观的目录,虽然他知道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即使读不了,有的书或许也根本找不到,但他说,至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过那么多有趣的书,过屠门而大嚼,不也是一种乐趣吗?
陆灏说,他最喜欢钱锺书的书。本来,陆灏只读书不藏书的,但在所买回的书中,钱锺书的《管锥编》,不仅有他熟读过的最早版本,精装本出来后他还是买了,文集出来以后他又买了,不同版本的《管锥编》陆灏就拥有了四种。陆灏说钱锺书聪明、有学问、有见识,读了很多书,并且读书完全是从兴趣出发,再寻找有兴趣的养分。特别使陆灏佩服的是钱锺书甚至能在枯燥的书中读出自己的趣味,能在一笔带过的内容中发现生趣。
“书房成了后缀词”
陆灏对藏书有自己的看法,大体是为读而藏。他最佩服的是钱锺书先生,家里几乎没什么书,学问都装在自己脑子里。最不喜欢的是那些书橱里整整齐齐摆放着漂亮的精装本,看上去一尘不染,却不曾开读的人。他说,清初学者周亮工的父亲,写过一篇《观宅四十吉祥相》,开头两句就是:“案头无淫书,架上无齐整书。”表明藏书、读书体现一个人的品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