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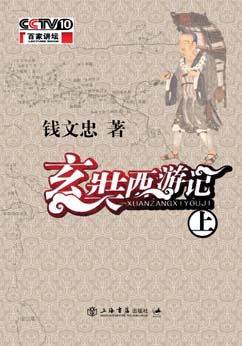 11月30日,以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玄奘而广受追捧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钱文忠,刚到西安,在小寨下榻的酒店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就历史迷雾中的玄奘,就自己的授业恩师季羡林,就一直心驰神往的西安,对记者娓娓道来。谈话中,他不断慨叹,玄奘这个历史伟人与文化伟人,被我们戏说得太久了,是该恢复他的本来面目了。 11月30日,以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玄奘而广受追捧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钱文忠,刚到西安,在小寨下榻的酒店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就历史迷雾中的玄奘,就自己的授业恩师季羡林,就一直心驰神往的西安,对记者娓娓道来。谈话中,他不断慨叹,玄奘这个历史伟人与文化伟人,被我们戏说得太久了,是该恢复他的本来面目了。
关于玄奘,他被我们戏说得太久了
记者:随着您在央视的开讲以及其他活动,有人称今年实际已成了“玄奘年”,对这位不远万里西行取经的高僧,历代也有着不同评价,港台一些影视剧也对玄奘有过戏说式的演绎,对这些您怎么看?
钱文忠:我在《百家讲坛》上讲玄奘,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关注面,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这样一位大家都觉得很熟悉的人,其实是个熟悉的陌生人,我想玄奘重新进入大家视野,这是最近一两年的情况,包括“重走玄奘路”等活动,人们愿意重新追念玄奘的精神,正符合了我们这个民族在进一步开放,去走向世界,去追求真理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历代对玄奘的评价,大多是被戏说化了的,而曾经诸如“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之类评语,也完全是建立在《西游记》等已对玄奘进行了娱乐化、游戏化后的文艺作品之上的,有的添加了一些笑料,对这个人物的阐述,显得他好像很窝囊,絮絮叨叨。而真实的玄奘完全不是这样。那种高僧大德的慈悲心怀,对佛法与人间真理的高深研究,在他身上,传统性与国际性达到了高度圆融统一的境地,他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度的文化财富,一个标志性人物,玄奘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
这就使我很是感慨,我们的历史人物本身就足够精彩,我们只要把他们真实地表达出来,就一定很精彩,有高潮,有低谷,大可不必用随意的娱乐化戏说。我们拥有的传统文化,不是太多了,而是实在太少,戏说应该有个底线,不能对这个人物有损伤。我们应该用敬畏、珍惜、呵护这样的态度去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不要太轻易、随意地去损伤它。用一种后代对待祖先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会比较好一点。
季老治学,是“入其室,操其戈而伐其人”
记者:您是季羡林的高足,18岁起便考入季老门下受教,近距离地接触了这位学界泰斗,“季门立雪”这些年来,季老的哪些东西使您受惠最多?有没有特别令您感动的小事?您能否谈谈季老在海外做学问的经历?
钱文忠:季老和西安特别有缘,有很多学生在西安。我跟随他那么多年,相信会受益终生。关于季老,可以举很多例子,但举再多例子,也无法形容出他那样的。我觉得老师有优秀与伟大之分,优秀的老师可以教给你具体的技能,他的方式可能是疾风暴雨式的,留给你非常明确的印象;而另一种是伟大的老师,他永远是这样和风细雨,让你如沐春风,在不知不觉中得到陶冶,受到启发与教益,季老便是这样一个伟大的老师。当然他首先是个伟大的学者,燕园中流传着他很多传说,如给学生看行李,还有他巨量的捐赠,他自己俭朴几近苛刻的个人生活等。我感受最深的是,季老到海外求学时,绝不做任何和中国学术有关的课题,因为有些人是在两头贩卖,出国后研究国学糊弄外人以拿文凭,回国后又以西方学问来到处招摇,季老则是“入其室,操其戈而伐其人”,入西方传统学术之室,操西方传统学术之戈,去解决西方学界最前沿的问题。跟随季老学了这么冷僻的一门学问,我不敢奢言发扬光大,我做不到承前启后,继承前人的可能有一些,但怎么启后呢?那得要有那么一批人愿意来学呀,哪有这么多人来学这么冷僻、没有功利的学问呢?所以说我更像是“守先待后”,守住先辈的东西,等待有缘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