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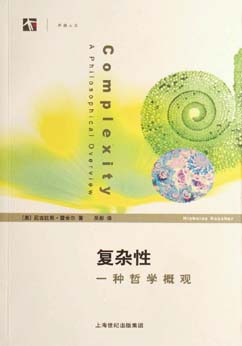 一枚受精的鸡蛋,如果保持38摄氏度的恒温,它将会孵化出小鸡;如果把它放在100摄氏度的沸水中,则会变成一枚熟鸡蛋;而让它经受60摄氏度的高温,它将会自发腐败,成为臭鸡蛋。事情就是如此奇妙,不到最后结果出现,就很难判定它的结局。 一枚受精的鸡蛋,如果保持38摄氏度的恒温,它将会孵化出小鸡;如果把它放在100摄氏度的沸水中,则会变成一枚熟鸡蛋;而让它经受60摄氏度的高温,它将会自发腐败,成为臭鸡蛋。事情就是如此奇妙,不到最后结果出现,就很难判定它的结局。
从某种角度而言,人类的出现也是一个奇迹。化石记录非常清楚地表明,并不存在某种中心线索以目标导向的方式引导从原生动物到人的稳定发展。相反,一直是连续和极端复杂的分支化发展。人类只是进化之树末节嫩枝的末端。也就是说,如果生物在其历史的任何阶段以及环境有所不同,那么现存的物种就将一定完全不同。
再来看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地球。地幔对流和板块运动,决定着大陆和海洋的格局;温室效应和臭氧空洞,改变着地球的环境;大气对流和海洋环流,制约着气候的变化。还有众所周知的蝴蝶效应。所有这些都表明事物的相互关联,这一切让人不由感叹造物的奇妙与复杂。
那么,该如何来面对这些复杂现象呢?《复杂性》的作者雷舍尔就认为:复杂性既是一种祸害又是一种福音。说它是福音,因为它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我们相伴,并成为发展过程的真正先决条件;说它是祸害,因为它自身既是消极的,又是一种阻碍我们顺利实现未来发展过程的重负。在我们的复杂性世界中,完全不存在确定的担保。正是这种不受欢迎又不可避免的境况,预示着理性的尴尬处境:合理性一方面要求我们去做“似乎是最好的”,一方面又要求我们充分而清晰地认识到这种要求实在是太过了。
不仅如此,有些看似非常简单的操作原理也会产生非常复杂的结果。就像一条河流简单地遵循“最小阻力路径”,但却描绘出蜿蜒曲折甚至盘旋回自身的河道。晶体遵循同样的规则,亦可生成非常不同而精致复杂的结构。国际象棋大师和初学者都严格按照相同的移动方式——单个棋子的行为完全相同,但表现的水平却全然不同。
在实践中,事情不大可能如想象中那么好。恺撒在自己的时代不可能知道宝剑里含有钨。在哈维认识血液循环之前,此现象就已经在人体中存在。在贝克勒尔发现含铀物质之前,它就具有放射性。亚里士多德时代的人也不可能读懂今天的物理学和宇宙学论文并从中获得乐趣与益处。一个7岁的儿童也不大可能领会成年数学家讨论的内容。
在原始社会,人们不能理解事物运作是如何能够危及一个家庭乃至危及一个氏族或者一个部族的。在现代世界,人为的巨大灾难,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就会危及数百万人,甚至可能危及我们这个星球上整个人类。一般都认为,技术进步使生活变得更轻松容易。乘飞机比坐轮船更快捷,打电话比写信传递信息更方便,用电灯比用煤油灯更舒服。但是即使所有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技术进步仍有其两面性。《复杂性》告诉我们:新获得的技术能力相应地带来了管理上的新问题,更多的选择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信息来作出决策。众所周知,现代小汽车有成千上万个部件,而航天火箭有超过600万个部件,只有技术专家才能对它们修理和改进。在20世纪50年代,当一架飞机从空中坠落,有两位专家就能很容易找出错误。但是,在1996年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00班机爆炸后,要确定这个复杂系统功能出现故障的原因,则着实使许多团队陷入了长期的困惑。在今天的战争中,飞行员在5分钟内作出的决策比航海时代舰上海军上尉一天内作出的决策可能都要多。
康德就强调了这种新问题不断“诞生”的现象。他始终认为,“任何事实问题的解决都进一步导致产生未解决的问题”。科学史也有力地证明了这种经验探索上的问题不断增值的原理。古希腊人发现了4种元素;在19世纪,门捷列夫发现了大约60种;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经发现了80种;而今天,我们掌握着元素稳定状态的一个巨大系列。现在公认的物理学的基本常量,从数量上看,只有1个是牛顿物理学时代的万有引力常数。第二个是在19世纪增加的阿伏加德罗常量。剩余的6个全都是20世纪的创造物:光速、基本电荷、电子的静止质量、质子的静止质量、普朗克常量、玻尔兹曼常量。此外,各种科学实验室也以给人印象深刻的、超过了过去百年的速度在增加。以英国为例,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不列颠群岛仅有11个物理实验室;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超过了300个;如今则有几千个。
科技的发展使我们的生活面临着无限种可能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事实比小说还离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