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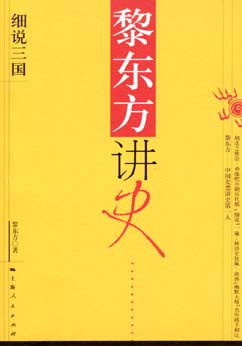 黎东方先生的讲史作品以《黎东方讲史》之总题重新出版了。其中的《细说三国》我又读了一遍,仍觉很有味道。易中天先生走红之作《品三国》,也是一部好书;粉丝如云,即为佐证。我听过“百家讲坛”中易先生的几段讲述,觉得不过瘾,第一时间买到他的书,一口气读完了。因为两部书在同一时间拜读,有时就拿两本书的同一内容作比较。应该说,两书各擅胜场。我这里想特别指出黎著《细说三国》的一些优胜之处,那就是:坚持史学的基本游戏规则,严格遵守时空常识,不随意发挥,不断章取义,不望文生义,不把戏剧平话充史事。现在,学者讲史很流行,很成功,但也有值得提高之处。我觉得,黎东方先生讲史作品的优长之处是值得当代的学者们——包括易中天先生——借鉴的。 黎东方先生的讲史作品以《黎东方讲史》之总题重新出版了。其中的《细说三国》我又读了一遍,仍觉很有味道。易中天先生走红之作《品三国》,也是一部好书;粉丝如云,即为佐证。我听过“百家讲坛”中易先生的几段讲述,觉得不过瘾,第一时间买到他的书,一口气读完了。因为两部书在同一时间拜读,有时就拿两本书的同一内容作比较。应该说,两书各擅胜场。我这里想特别指出黎著《细说三国》的一些优胜之处,那就是:坚持史学的基本游戏规则,严格遵守时空常识,不随意发挥,不断章取义,不望文生义,不把戏剧平话充史事。现在,学者讲史很流行,很成功,但也有值得提高之处。我觉得,黎东方先生讲史作品的优长之处是值得当代的学者们——包括易中天先生——借鉴的。
讲史必须要有时空概念。通常我们讲古史,是以纪年为界定的,月日可以不计,那也说得通,但有些月日就须注意了。黎著就相当注意某些特殊年月,如建安元年(196年),一般史书就将它作为曹操迎献帝都许县,改元建安,即以为本年元月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始,而黎著则标明曹操是本年八月才到达洛阳,八月辛亥日取得支配中央政府大权的。这个月日如忽略了,容易误会曹操早就捞到大权了。《三国志》的三个组合部分《魏书》、《吴书》和《蜀书》,其素材,甚至是若干纪传并非出自陈寿一人之手,所以三书同一史事的文字也多见相悖处,如《魏书》说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的事,载在董承为曹操所杀之前,而《蜀书》恰相反,说董承被曹操杀了以后,刘备才杀车胄。《三国演义》宗《魏书》说。但黎著却据刘备老练、沉着而又世故、富有韬晦的性格,认为《蜀书》的记载是对的。“董承先在许县被捕,刘备才着了慌,提前对曹操翻脸,占领下邳杀掉徐州刺史车胄。”这样推断该是准确的。
《品三国》若干细节就忽略了时空概念,造成不应有的失误。如说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称汉中王,还师成都,“这一连串的好消息让刘备集团的人大受鼓舞,再加上孙权正在东方进攻合肥,关羽便趁着这大好形势,发动了夺取襄阳、樊城的‘襄樊战争’”(《品三国》(下)第83页)。其实,当时东线无战事,孙权在曹操生前,最后一次进攻合肥是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也就是《三国演义》所述张辽威震逍遥津那段战事后第二年的濡须坞之战,此后,孙权请降曹操,报使修好,此后直到关羽北攻襄樊,吕蒙白衣渡江,双方足足有三年未发生战争呢。
讲史很忌随意解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有说关羽斩颜良后的一段史事,“遂解白马围,徙其民,循河而西”,这句话,说白了应是:曹操于是解救了白马津的围困,将当地民众迁移,沿着黄河西走。黎说也作通常解说:曹操解了白马之围,救出刘延与刘延手下之兵,合起来,沿着当时黄河的南岸向西而去。将当地民众迁移,自己与白马守兵西走,都讲得通,但不能说带着民众一起走,让自己背上沉重包袱。由此我觉得《品三国》解说得有些问题:“曹操解救了白马以后,料定袁绍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反扑,也一定会拿白马的老百姓出气——屠杀。于是带着白马人民,沿着黄河往西走(人们都知道刘备撤退的时候带着老百姓,不知道曹操也是这样的)。”(《品三国》(上)第86页)当时各家军头确有争夺劳动力的努力,但曹操在后有强大追兵时还带着“白马人民”,如此境界?我觉得这不合战争常识,也不合曹操性格。《品三国》说“周瑜的仗打得确实漂亮。赤壁之战中,他是孙刘联军的前线总指挥”(《品三国》(上)第3页),很不准确。《三国志》有关史传,如《蜀书·先主传》,足征双方自成体系,相互配合,有事协商,独立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