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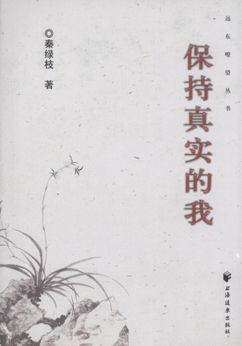 这是一本小书。书中收集的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小文。 这是一本小书。书中收集的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小文。
我是个报纸编辑。从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时起,编了十几年的副刊“夜光杯”。编辑是为人作嫁衣的,但出于一种内心的冲动,有时为了版面的需要,自己也试着写一些东西。各种各样的,连补白也写。这还是一种老传统,当年我的前辈如张恨水、张慧剑、唐云旌、姚苏凤诸位先生编副刊时,就常常自己动笔,不写就手痒,意不能平。有人认为这是利用职权,霸占地盘。我觉得话不能这样说。报纸副刊要贴近现实,贴近生活,乃至与时事相呼应,在来稿中找不到一篇能符合这种要求的文章,只好自己“操觚”了。
我在“夜光杯”的版面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先叫“休息时断想”,后改“不拘小记”,笔名叫“秦绿枝”。本书中有一篇《生活在中下层的声音》,可以看作是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专栏,为什么要用“秦绿枝”这个笔名的“招供”,这里不再饶舌。
除了这个专栏,我也写别的文章。其他报刊也时来约稿。有一年,《监察与廉政》(后改名《清风》月刊)还特地为我辟了一个“廉政断想”的专栏,真不好意思,勉力应命。如此日积月累,长长短短,发表在本报的,借光于他报他刊的,究竟有多少,我也没有认真统计过。但报人为文,常有应时应景的“速朽”之作。现在我选编的是自认为还能经得起时间考验,读来还有些余味可供咀嚼的,至少还有一些想法可以引起别人共鸣的部分“敝帚自珍”的“藏品”,是否真有可读性,只有请读者鉴别了。
我想,读者还不难看出,这本小书还有个掩饰不了的个人意图,就是我的还不成气候的“杂”。新闻出版界的一些前辈老先生都提倡过编辑应该成为“杂家”,我自己也信奉这一点。但“杂”也要“杂”得有水平,这决定于学问的深浅。但做学问是要一辈子倾力以赴的事情,成绩如何,最好还是让别人来评估。自己一年一年地过下去,只要不是太荒疏,回首一看,毕竟多多少少总有长进吧。
因为“杂”,这本书分了几个门类,写人的,写事的,写书的,写情的,等等。比如写人的,既写了健在的,也写了逝去的。我用了一个分类标题:“朋友最可珍惜”,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越到老越觉得朋友的可贵,而且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书中收录的一篇《我看周少麟》,可以看作是新朋友中的一位知交。周少麟是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的长子,读过大学,再学京剧。前几年他从海外回国定居,我们时有来往。少麟对周信芳的艺术(麒派)有他自己的见解,与时下一般学麒派谈论麒派的人不大合拍,尤其在一些会议上发表的言论往往令人惊诧,因而招致了不少误解。我写的这篇小文是根据我自己对麒派的认识,从而为周少麟作了一些辩解。少麟看了此文,颇受感动,我们的感情也更加接近了。
另一个分类标题:“往事时刻萦怀”,一看就知道是写事的。我这人一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过去,回忆录之类,以前不会写,以后也不会写。但有时触景生情,在逝去的岁月中有些零星片段的故事,也还有点思念的价值,碰到有必要,就写下来发表了。
写感情的那些东西,是坦陈我老来生活的其他侧面,也暴露了我的思想品位。
很久以来就提倡说真话。真话是不是都可以说,还要看情况而定。但做人应尽量真实一些,是可以时时自我勉励的。其中有篇小文叫《保持一个真实的我》,我很喜爱。忽然触机,就用来做书名,《保持真实的我》(近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似也能概括这本小书的全貌。
(本文是作者新书《保持真实的我》的前言,内容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