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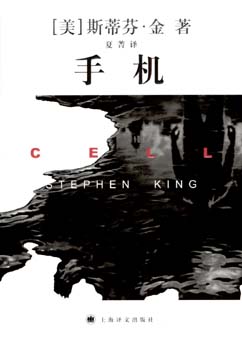 假如现在有人告诉你:所有受到过手机辐射影响的人在一刹那间都会变成疯子,你会有什么反应?你肯定相信这个人是个精神病人,或者,你安慰自己,用手机的人那么多,即使变成疯子也不是只有你一个。总之,手机远远没有让你惧怕的威慑力。但是,假如这一切是真的,会是怎样? 假如现在有人告诉你:所有受到过手机辐射影响的人在一刹那间都会变成疯子,你会有什么反应?你肯定相信这个人是个精神病人,或者,你安慰自己,用手机的人那么多,即使变成疯子也不是只有你一个。总之,手机远远没有让你惧怕的威慑力。但是,假如这一切是真的,会是怎样?
斯蒂芬·金的这部关于手机的新作,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问号。小说中,手机带来了一幅末日的画面——所有受到手机脉冲辐射的人突然在一刹那间开始失控,像动物一样互相撕咬,所有的破坏力都释放出来,到处是死人,到处是断壁残垣。故事就从这样的末世景象出发,讲几个不用手机得以逃脱手机脉冲破坏力的人,如何在这场手机变异的灾难中幸存下来的经历,情节诡异。
长久以来,这位恐怖大师的小说一直居美国畅销榜的上座,《手机》是继2002年他宣布封笔之后推出的新作之一,它向人们说明:斯蒂芬·金宝刀未老,江郎并未才尽,身手依旧不凡。这部在科幻类小说中高居榜首的作品势必为好莱坞的电影公司所欣喜,小说塑造的氛围、场面和情节充满了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惊悚效果,那种强烈挑战感官刺激的因素必定能一如既往地成为票房灵药。尽管自9.11以来,美国人民对灾难的承受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对“劫难”题材的挖掘依旧是一个显示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功夫。我们平常看恐怖片的经验是,越是日常生活常见的东西越能把恐怖深入人心,《手机》就是这样一部提高惊悚“段位”的作品。
像我国这样的手机大国,手机的使用量是很庞大的。作为现代科技生活的代表之一,手机给了我们随时随地化天涯为咫尺的方便,用惯手机的人们很难适应没有手机的生活。当有一天你因为不用手机而感到无所适从时,一种异化已经从此开始。
斯蒂芬·金据说是个拒用手机的人,因为深信“手机”是这个时代给人的最大镣铐,于是,他把科技渗入日常生活的控制力铺展开,就给了我们如此触目惊心的恐惧,这种恐惧平日里被我们忽略,而正因为忽略才越发彰显。在这里,人脑像电脑一样可以被“格式化”,可以“清空”“内存”,输入“屠杀”的指令,可以“激活”被压抑至最底层的本我,所有这些电脑中常见的处理方式一旦应用于人,一座现代的“所多玛城”就诞生了。
《圣经》中的“索多玛”和“娥摩拉”是人类对于劫难想象的一个极点,《手机》中也用了这两个城的譬喻,其中多少包含了斯蒂芬·金对于现代科技文明的疑虑。
这种疑虑在西方影视作品中并不少见,“异化”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技术文明的质疑。斯蒂芬·金沿用这种思路,不过,他指出了最让我们胆战心惊的“异化”——假如你身边的“手机”是一颗定时炸弹,你是否还敢面对它?手机的应用是为了人们沟通彼此的需要,而一旦这个“巴别塔”全盘崩溃,人类变成行尸走肉,根本无法沟通,技术的利刃就会反过来深深地伤害自己。
《手机》出自一位讲故事的高手。同故事中的情节一样,讲故事者本人堪称一部传奇。三十几年的写作生涯,斯蒂芬·金的名字就是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招牌,最高记录是四部小说同时登上畅销书榜,创造了一个书业神话。作为“恐怖小说”的行家里手,斯蒂芬·金倾力于挖掘一片未知的黑暗领域。
不管科学如何进步,技术如何发展,这片未知的领域就像影子一样,始终不会消失,这构成了人们恐惧的根源,也是“恐怖小说”俘获人心的根源。
斯蒂芬·金小说的畅销为很多人所不屑,正统文学界始终将他的作品排斥在严肃文学之外,以至于2003年“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宣布斯蒂芬·金获得全国图书奖的“终身成就奖”后,举国哗然。一贯维护精英文学正统地位的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公开声称这是“可怕的错误”,评委是一群白痴。这样的“大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对单纯的读者而言,这种分野并没有什么意义,重要的只是:这是不是一个好故事,讲得是不是足够吸引人。对于更多人而言,斯蒂芬·金就是那部让人印象深刻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作者。他的作品远非完美,但常常打动人心,这就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