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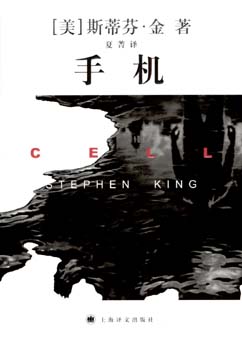 在前一本面世的《尸骨袋》中,斯蒂芬·金写到遭遇创作瓶颈的畅销作家在银行保险库里有好几本现成的小说,有如“合格的松鼠储存了果实”,在大半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的情况下照样能够从秘密箱子里取出一本来出版。不过,读者可以放心,这本完成于2005年的《手机》绝不会是过期的“果实”。因为在恐怖之王的前半生里,根本没有手机这样东西。 在前一本面世的《尸骨袋》中,斯蒂芬·金写到遭遇创作瓶颈的畅销作家在银行保险库里有好几本现成的小说,有如“合格的松鼠储存了果实”,在大半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的情况下照样能够从秘密箱子里取出一本来出版。不过,读者可以放心,这本完成于2005年的《手机》绝不会是过期的“果实”。因为在恐怖之王的前半生里,根本没有手机这样东西。
书中说,“据说中国的手机数和美国人口一样多,你能想象吗?”不需要作家去想象,科技产品的扩张必定铁板钉钉地描绘在市场蓝图上了。作家想象的恐怖是繁荣市场背后的未知领域。科技改变生活,自然也会改变人类的恐惧形态。传统的鬼屋、僵尸、异类生物体、世界末日……虽然它们依然生龙活虎地存在于幻想派作家的头脑中,但与时俱进的恐怖小说总免不了半只脚踩进科幻小说的边界内。科技日新月异,人类迫不及待追逐科技的姿态恰好是一种新迷信,狂热、盲目,这种激流般的群体意识也必然有其阴暗面,好比科技本身也在发达的同时暗暗扩张可怕的漏洞。这本相当贴合现实、又看似极端荒谬的小说仿佛毫不留情地“哗啦”一声撕下科技光鲜的表皮,露出人类并未被科技改变的本性,尤其是本性中最可怕、最脆弱之处。
我比较了近期出版的斯蒂芬·金三部作品,确定这部《手机》是最地道的恐怖小说,走的是经久不衰的僵尸派路线,他惯用的红袜队、流行音乐等元素也一样不缺,当然最关键的是:一如既往地用人类之爱抗衡无解的恐怖。
小说第八页就已经进入骇人听闻的人吃人攻击场面,即便是在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中,也算得上快节奏。因此,华盛顿邮报“这本书一拿起就放不下”的赞誉就不难理解了。在书中,美国人民在接听手机时无一例外地被脉冲洗脑,成为行尸走肉,头脑和意识就像被格式化的硬盘一样,还原到零;但恐怖的不在于“零”之虚无,而是作为“零”的求生欲望,亦是文明花了千万年改造的残酷而野蛮的本能,事实上,这种改造或许永无尽头。
不用说,这时候的幸存者与拯救世界的英雄便是不使用手机的人群,大都是婴幼儿、老人和刚好走运没在那时候用手机的成年人,大批大批的时代精英、赶时髦的青少年都成为手机牺牲者。手机变异人迅速拥有了新型的思考能力,超自然的心灵感应能力超强,甚至企图召集幸运者,诱使他们打电话给亲人,从而灭绝人类——这一招着实狠毒。我绝望地想到:科技若变异,便是不仅以人为本,还以人为武器了。
负隅抵抗的幸运者包括漫画家克雷、丧母的少女爱丽丝、有点娘娘腔的爱猫男人汤姆、正直老派的老校长、机灵的男孩乔丹、不得不自我牺牲的雷、勇敢的孕妇德妮丝……正所谓“以毒攻毒”,对付未知的手机末日的唯一办法终将归结为手机本身、科技本身,而人类情感也将在灾难时分显示巨大的力量,团体的合作和信任同样至关重要。我们看到斯蒂芬·金一贯擅长的群像描写手法再次发挥了魅力:电脑儿童乔丹头脑清晰,代表着电脑和人脑共同思维、熟练于科技联想力的时代特色,早夭的爱丽丝用一只耐克婴儿鞋本能般地转移恐惧,主人公克雷则仿佛人类之爱的代言人和善于就地取材改革武器的技术能人,德妮丝似乎象征了未来希望……虽然依然是典型的“小人物拯救大地球”的模式,但这一模式得以经久不息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和小人物惺惺相惜,故而易于感动。
手机对大脑是否有害?这可不是这本书要讨论的问题。斯蒂芬·金没有让这个故事成为简单的“反科技”之作,故事的走向不在于小人物誓要拯救地球,也不是夺一条活路那么单一。对亲人的固执爱念构成了正面力量,克雷在末日始终难忘妻儿的安全,甚至放弃与同伴逃离险境的机会,独自游荡于荒芜可怖、浩劫后的世界,只为了和儿子相依为命。哪怕血腥场景俯拾皆是,在野蛮和卑鄙之外,有无奈与无力,终究还是有悲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