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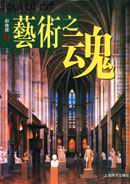 在我所住的上海浦东,有一家很小、很简陋的歌舞厅兼剧场,观众绝大多数是建筑工地的民工。在饱暖之后,他们迫切需要艺术来消遣、娱乐。这才是艺术世界存在的根本理由之一。 在我所住的上海浦东,有一家很小、很简陋的歌舞厅兼剧场,观众绝大多数是建筑工地的民工。在饱暖之后,他们迫切需要艺术来消遣、娱乐。这才是艺术世界存在的根本理由之一。
有一回我经过那里,也买了一张门票(20元)和民工兄弟一起进去在烟雾腾腾中同乐。当然我还有另一个隐蔽的打算或动机:作为观众的观众,或一位冷静的旁观者,不仅看台上,也看台下,而且是凝神观照,不仅仅是用肉眼看。
由河南郑州一个不入流的歌舞团在演出。
8名妙龄少女,三点式的大腿舞,晃了四幕,直把两百来名民工兄弟(其中也有60来岁的观众)看得目不转睛,心潮激荡。之后是流行歌曲上场。
老板就坐在大门口,兼验票员。经营演出是他的生计。俗话叫混口饭吃。他可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更不是用大众艺术去越狱逃跑。
那些来自农村的村姑们在台上的动作有自得其乐、表现自我的成分。主要恐怕是为了赚饭吃,即用踩着节拍的、挑逗的性感大腿去同民工兄弟交换些金钱。
台下的观众在工地上苦力干活一周,想在这里放松两个半小时,是天经地义的合理合法和必需。其实这在本质上也是越狱行为。
在整个演出过程中,我经常环顾四周(前后左右)的台下观众,尤其是观察民工兄弟的眼神、表情和流露出来的陶醉灵魂状态。——这时候,我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局外人。我思考的是艺术的本质。
是的,当我走进艺术世界这个大剧场的时候,我扮演的是双重角色:
观众或看客;
观众的观众,或看客的看客。
只有这后者——旁观者——才是哲学层面。
读者手中这部书稿是我多年冷静旁观的结果:
“我冷静旁观,故我在。”
最后,关于我的写作心理状态,我想在这里交待几句:
自始至终,我都处在一种发愤闷或发悲愤的状态。这便是对“生老病死 ”这个大框架的冲决。写作成了我冲决、以牙还牙的唯一方式和手段。我不是写,是哭。是心在哭;悲愤借哭泣而出。哭“生老病死”的荒诞结构。尤其是在写欧洲墓地艺术这一章的时候。
每当我完成一部书稿,内心便有一种自由、解脱和越狱成功的感觉。但这感觉决不会超过一天,我又会重新陷入原先囚犯的心理状态。这便是我所说的再度被捕入狱。于是我又不得不去构思一部新作。
多年来我意识到,我的生存状态原来是在这条悲壮的链上:
大牢里——越狱——重新被投进大牢——再次越狱——……
这是我的命中注定,也是我的最好生存方式。
迄今为止,我的49部大大小小的作品都是我在这条链上的可靠见证和忠实记录。
“啊,我在大牢墙上挖洞,故我在。”
若干年后,当死神来敲我的门,我希望我不在大牢的墙内,也不可能在墙外,而是在挖洞的过程中,未完成式。
在本质上,艺术、科学和哲学的世界都是未完成式,不会有最后一个句号。
最后我还想交待一句我撰写这部书稿还有一个动机:
纪念我走进艺术世界、开始形成世界观50周年。到2007年冬天,便满整整半个世纪。这几乎是我一生。
1957年冬天,反右结束,我受到处分,加上初恋失败,冥冥中有束内在的光引导苦闷、压抑中的我跑到北大朗润园美国教授、莎士比亚专家温德家去欣赏西方古典音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到今天。
所以这部书稿是我同艺术世界半个世纪交往的总结。更为重要的是,后来我把美作了推广,它包括科学美、艺术美和哲学美。
正是这三大美充实了庄子的空筐:“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并塑造了我这一生。
我一无所有,既无权,也无势,钱并不多,是个标准的中国中产阶级小康。我只有生生死死追求庄子空筐里的三重美。
2005年暮春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6年早春最后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