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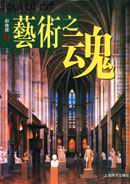 如果我这部书稿也勉强算是一座三、五层的混凝土建筑,那末,它便是由以下多块基石奠定、支撑的: 如果我这部书稿也勉强算是一座三、五层的混凝土建筑,那末,它便是由以下多块基石奠定、支撑的:
两千多年前庄子用他的哲学智慧和想像力举起了一面鼓舞人心的崇高美学大旗:“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它是一个伟大的“空筐”,需要日后的科学、艺术和哲学活动去不断地填满。永远也填不满。
每一件够格的艺术作品结构都呈“空筐结构”。
这是我受纯粹数学的启发提出的一个美学命题。
艺术哲学的最高原理之一是极值原理。
这是我从微积分借来的。
人类追求艺术的根本心理动机之一是越狱逃跑。的确,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越狱的动机更勇猛、更冲动的吗?那是生与死的一种必要性。
另一个与之平行的基本动机是对“真善美”的追求。
这是老问题新看,是朝古老课题投射出一束新的亮光。太阳底下常有新事。
我理解的诗文和美是广义的。于是便有了科学美、艺术美和哲学美。其实科学美和哲学美也是艺术美。
我国艺术哲学家叶燮(1627—1703)的一些命题是我的立脚点:“天地之大文,风云雷电是也。变化不测,不可端倪,天地之至神也,即至文也。”
他把天地自然之文看成是诗文的极至,为至工者。
提出“造物之文章”这个美学命题是叶燮的创造。
在适当的地方,我要把它展开,包括他的这个命题:
“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
这是有关广义美的一个定义。 我的意图仅仅是把它作为我的出发点。我要尽力拓展它,充实它,丰富它,用统一和较高的审美把科学、艺术和哲学这三大领域一一收拾、穿纽,成为一条金项链上的三颗钻石。
我提出“泛陌生化”概念。它越出了文学艺术领域,波及到了科学和哲学范围。它成了整个人类文明之旅的一种统一的、普遍世界的结构和律动:
熟悉的世界——将熟悉的世界予以陌生化——新世界——熟悉的世界——再将熟悉的世界予以陌生化——新世界……
艺术家、科学家和哲学家是为了冲决、打破熟悉的世界而来到世上走一遭的。
一部世界艺术史、科学史和哲学史可以为上述链作证。
哲学思想或概念决定、规定了艺术语言的基调。
艺术是帆,提供动力;哲学是舵,指出方向。
至于建筑物同基石的关系,不外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基石是花岗岩,很坚实、过硬;建筑各层秩序井然,既和谐、匀称,又合比例,显得壮丽。这叫上下相称。
第二,基石可靠,但建筑物干瘪、单调、杂乱、丑陋。这是上下不相称。
第三,基石不可靠,建筑物必坍塌。这是空中楼阁。
读者手中这本书究竟属于哪种情形,要由读者来评判。
当然,我的目标是尽力走近第一种情景。这是我的一本美学哲学著作。重点在西方。
至于写作风格或叫手法、文风,我则使用较轻松、自由的散文笔触。因为在哲学领域,我是个“散文随笔派”。
谈哲学的时候,一定要板着脸,正襟危坐吗?
坐在海边山坡,用长笛或黑管把艺术哲学原理像牧歌那样缓缓悠悠、抒情地吹奏出来,不是更好些吗?
当然,论述哲学时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要有英雄气象:
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
(选自《艺术之魂——我爱艺术,故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