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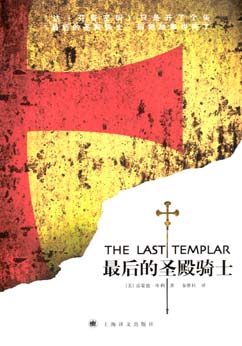 读翻译小说,文化背景的了解必不可少。“圣殿骑士”对中国普通读者而言,的确需要进行一番名词解释和历史普及,或许在西方这段历史也有些支离破碎。因此《最后的圣殿骑士》在小说卷首就用耶路撒冷陷落的战场搏杀,进行了浓墨重彩的“预热”。通常,小说中这类“序幕”式的一个情节、一个场景,犹如宴席上的“开胃菜”一样,不值得多花心思。可《最后的圣殿骑士》则不然,它是小说叙述情节的复调结构之一。由此可见这部惊悚小说的与众不同。 读翻译小说,文化背景的了解必不可少。“圣殿骑士”对中国普通读者而言,的确需要进行一番名词解释和历史普及,或许在西方这段历史也有些支离破碎。因此《最后的圣殿骑士》在小说卷首就用耶路撒冷陷落的战场搏杀,进行了浓墨重彩的“预热”。通常,小说中这类“序幕”式的一个情节、一个场景,犹如宴席上的“开胃菜”一样,不值得多花心思。可《最后的圣殿骑士》则不然,它是小说叙述情节的复调结构之一。由此可见这部惊悚小说的与众不同。
中世纪的圣殿骑士在苏丹军队的围攻下,派两人突出重围,目的是保存一个精致的小盒子。七百多年后,四名身披圣殿骑士白色披风,用带面罩的头盔蒙面的骑士,骑马闯入正在举行梵蒂冈珍宝展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抢去了展品中一个中世纪的密码机。小盒子与密码机,是作者雷蒙德·库利精心设下的悬念,诱惑读者乖乖地跟他走,听他讲一个虚幻的故事。故事里有影视剧中常见的飞车追踪、废墟逃生、潜水探宝、海岛相争等惊悚火爆的场面……血腥和杀戮等商业电影中常见的情节元素一概俱全。作为影视编剧,雷蒙德·库利轻车熟路,玩得得心应手。《最后的圣殿骑士》的情节线索,就这样在警匪片的节奏中行进。当然另一个历史故事——作为小说悬念之一的中世纪圣殿骑士带着那个小盒子的神秘使命——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不同的是中世纪的生活节奏与现代社会不相吻合。如果后者的推进似枪战场面般火爆,那么前者的叙述旋律则是考古挖掘式的细腻,因为悠长的历史岁月只有这种节奏表现才适合,而且有宗教般虔诚的氛围。
惊悚小说与寻宝故事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英国作家斯蒂文森的《金银岛》、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以“寻宝”元素的加入,使儿童日常生活也变得悬念重重、趣味盎然。《最后的圣殿骑士》注重的是历史悬案,这也是从《达·芬奇密码》大红大紫之后,小说写手们争先恐后、一拥而上的新路径。这条新路上悬案化身为谜语和密码的混合物,小说人物的行动就是用头脑进行破译的过程。所以,暗地跟踪,夺命追杀,如此这般商业片中赢得眼球的招数,如今都成为惊悚小说中的调味品,只是为了调节气氛匆匆登场,匆匆下场。历史悬案才是主角,哪怕语气再慢条斯理,脚步再悠然自得,也无关紧要。小说中反派人物也不再是天生的强盗恶棍,而是高智商的社会上层人士,他们之所以站在小说中反派的立场,均有个人极其正当的理由。正义与邪恶的交手,人物性格的成因,由此而呈现多重色彩。
《最后的圣殿骑士》中,特工赖利和考古学家特斯的破案行动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那个七百多年前精心保存下来的小盒子内装的东西,有可能动摇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基石。科学求真的精神与千百年来稳定的、引导人们积极向上的崇高价值观相悖,怎么办?这是个两难的选择。倘若“真”无法与“善”携手,“美”又从何而求?《最后的圣殿骑士》尽管是一部小说,允许虚构,然而这个虚构的话题却犹如一个“结”难以解开,直到小说结尾,还是留存在读者脑海中。难怪西方评论媒体称“书中有关真相与科学、史实与悬疑的讨论撩人心弦,它的深度在一般流行小说中是罕见的。”
毫无疑问《最后的圣殿骑士》是畅销书,它是用浓重的商业意识精心包装的故事。紧张的情节,纽约、土耳其、梵蒂冈、希腊各地的风光,十字军时代的历史场景和密码学、宗教学知识让读者目不暇接,可一旦悬念的谜底揭晓,故事凸现出一个引人思索的内核。它冷峻地逼着你思索,让你认定它提供的答案是无奈的,存在着很大缺陷、却是眼前最适合的,编故事能力的高下就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后的圣殿骑士》超越了一般惊悚小说。生活中“真和伪”,“善与恶”并不泾渭分明,而商业和文化同样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进行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