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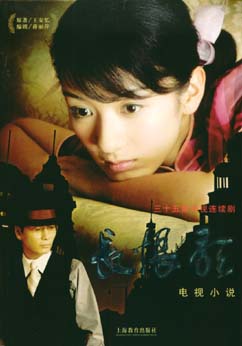 今天的文坛上,对关怀人的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念。有一种声音强调,要充分认识丰裕年代的写作现实,不能总是靠描写无告的小人物,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弱势群体,市场时代的落伍者来体现人文关怀,不要总是搞苦难崇拜,把贫穷神圣化和道德化;可另一种更为强大的声音却认为,人文关怀怎么能不通过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怀来体现呢?这是现实主义的根本。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把表现哪些人的问题看作唯一重要的事情或者首先重要的事情。时代已经发生巨变,“人民”的涵义也发生了变化,现实主义文学也在变化。我更主张一种开放的吸纳了多元方法的某些积极元素的新现实主义。对弱者,关怀他们的生存;对强者,关怀他们的灵魂。 今天的文坛上,对关怀人的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念。有一种声音强调,要充分认识丰裕年代的写作现实,不能总是靠描写无告的小人物,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弱势群体,市场时代的落伍者来体现人文关怀,不要总是搞苦难崇拜,把贫穷神圣化和道德化;可另一种更为强大的声音却认为,人文关怀怎么能不通过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怀来体现呢?这是现实主义的根本。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把表现哪些人的问题看作唯一重要的事情或者首先重要的事情。时代已经发生巨变,“人民”的涵义也发生了变化,现实主义文学也在变化。我更主张一种开放的吸纳了多元方法的某些积极元素的新现实主义。对弱者,关怀他们的生存;对强者,关怀他们的灵魂。
关怀人的问题应该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还是产生了一些具有较高精神价值的长篇小说,其主要特点是,一些作家在不同的视角下,冷静地关注真实的中国的人生,把关怀人的问题看得比关怀哪些人的问题更为重要,使得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在较为普遍和较为深刻的层面上触及到了关怀人的大主题。
张洁的《无字》以90万言篇幅书写三代女性的命运,她所倾诉的既是女性特有的痛苦,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悲剧,以个人化方式进入,达到群体化的深沉反思;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关注了一种政治行为下对以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的一代中国人身心的折磨和摧毁;王安忆的《长恨歌》关注的不只是一座城市,更是男权社会里都市女性囚笼般的人生和梦想折翅的哀怨;熊召政的《张居正》固然是写历史,但试图改革的人始终逃不出人治体系的可怕制约,实乃人的无助的悲剧;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巨大苦难和苦难人生的简单和偶然;雪漠的《大漠祭》关注生存本身的艰辛、顽强和苍凉;阿来的《尘埃落定》自由舒展地审视着土司家族及其相关人群的人性焦虑。不管这些作品关注的是些什么人,不管这些作品具体以哪个阶层哪种身份的人为对象,无论他们高贵还是卑微,笨拙还是聪慧,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都在深切地关注着真实中国的真实人生和不安灵魂。
然而,今天的文坛上,对关怀人的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念。有一种声音强调,要充分认识丰裕年代的写作现实,不能总是靠描写无告的小人物,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弱势群体,市场时代的落伍者来体现人文关怀,不要总是搞苦难崇拜,把贫穷神圣化和道德化,例如,是否应该正视已然形成的中产阶级,他们也在打拼,他们更多地表现出自信、智慧、财富、成功,和一套全新的生活价值观,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新的时代精神。难道表现这样的人就不是直面现实,就不是人文关怀了吗?可是,另一种更为强大的声音却认为,人文关怀怎么能不通过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怀来体现呢?这是现实主义的根本。自批判现实主义以来,一个最深刻的传统,就是对小人物,无告的人,平民,普通人,尤其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关怀;如果离开或者抛弃了这一点,不再为他们的疾苦呐喊,那还能叫现实主义吗,那还是富于良知的文学吗?最近,《那儿》——一部比较直露的意念化倾向明显的小说,却引起较强烈的反应,它的形态是一种久违了的“工人阶级写作”,它痛切地为被遗忘和被冷落的人群呼喊,为国有资产的流失痛心疾首,说明这种传统的根子很深。事实上,像《国家干部》一类小说,虽然不及《那儿》那样的激烈,所表现的是一种基本相近的价值取向:关注现实,关注政治,关注底层,愿做弱者的代言人。所以,问题是如此尖锐,甚至涉及到了谁是主角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把表现哪些人的问题看作唯一重要的事情或者首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诚然,我也认为,应该对“沉默的大多数”投注更多的关切目光,文学应有充分的底层意识,因为他们是大多数。但是,决不能说,只有写了底层,平民,弱者,农民,无告的人,才叫现实主义,别的都不是。时代已经发生巨变,“人民”的涵义也发生了变化,现实主义文学也在变化,我更主张一种开放的吸纳了多元方法的某些积极元素的新现实主义。所以,关怀人的问题不需要附加外在条件。毫无疑问,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阶级性”在淡化,“人类性”在上升。这里不妨举例来说。去年是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纪念。在虚构性文学方面(纪实类创作有所不同),我们似乎拿不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像样的作品。恕我直言,有些作家没有对人类大痛苦、大创伤的基本感觉,好像忘了给人类造成深重灾难的这个永久的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作品,太看重具体条件下的派别和集团的复仇与胜负,很少上升到人类关怀的层面,于是很难写出让全人类共同感动,表达了共同的痛苦、共同的屈辱和共同的承担的作品。而那样的作品,比如俄苏的,欧洲的一些作品,会让人真实地感到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息息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