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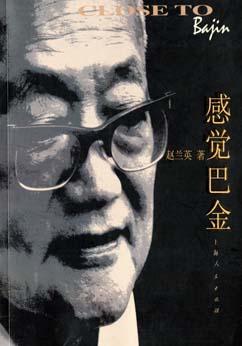 鲁迅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凝聚起来的最宝贵的硬骨头精神,尤其是他晚年杂文中所焕发的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社会良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无人能够企及。 鲁迅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凝聚起来的最宝贵的硬骨头精神,尤其是他晚年杂文中所焕发的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社会良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无人能够企及。
鲁迅在1936年10月去世以后,面对文学领域留下的巨大空白,有人试图重新选定一个作家作为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抗战前冯雪峰曾企图去接近和争取周作人;后来周恩来又选定了流亡日本的郭沫若来领导文艺界的抗战活动。周作人的散文写作与郭沫若的社会活动,都是各有其重大贡献于文学史的,但事实上,鲁迅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凝聚起来的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硬骨头精神,尤其是他晚年杂文中所焕发的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社会良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无人能够企及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是不能用册封的形式来选定的,它只能在自然而然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且是在风雨相伴中经受考验。
我们所谓的鲁迅传统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抗战以后,由于统一战线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精神传统的形态也必然地发生变化,它虽然不可能以战前的方式来体现,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它依然是凝聚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核心力量,总是会通过貌似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这已经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实践的道路所证明。我们只有确认了这些基本的特征,才有可能对于巴金的写作与文学实践活动的意义有所理解。
鲁迅精神传统的主要内涵,是特立独行于文坛、毫不妥协的现实战斗精神,并非个人的反抗而是随时随地团结各种反抗力量、发掘新生力量、扩大自己战线的战斗策略,贴近日常生活、于社会文化的细节中揭示民族悲剧实质的视角,这是鲁迅战斗传统最为重要的生命核心,也是它的活的灵魂。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鲁迅精神,没有群体的批判实践也不是鲁迅的批判策略,而脱离了社会生活的日常文化细节一味作高谈阔论,更不是鲁迅所认可的批判方法。鲁迅是极富有专制体制下反抗经验的人,他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在中国所面对的黑暗势力是何等的强大,凭着热情与勇敢是决不能胜以对方的,所以他对于暴虎冯河之类的莽撞做法一向嗤之以鼻,这也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煞费苦心寻找同盟军、布成统一战线的原因所在。而这一点,正是激进而且“左”的可爱的青年们决不肯给以理解和原谅的。再者,鲁迅的批判精神始终是从社会实践为出发点的,总是从具体事件的斗争上升为一般批判精神,所以他一再拒绝出国去做流亡寓公,宁肯不顾危险站立在他所深深热爱却不得不接受其怨恨相报的现实社会当中,与旧势力进行面对面的肉搏战。这也是他后来放弃功成名就的小说创作而转向招人讥骂的杂文写作的原因所在。
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各自的社会理想又重新鼓舞他们离开文学创作,转而写作反思社会历史、反思民族弱点的战斗性杂文,在无情的批判与自我批判中成为当代中国良知的代表。但是巴金与鲁迅相比,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巴金在文学写作的道路上,有许多地方都与鲁迅相似。他们在走上文坛前都接受过某些西方的社会思潮,并且以此为旗帜投身于社会运动,也都曾经因为理想的失败而陷入深刻的绝望。后来他们以小说创作著名于文坛,成为新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作家。然而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各自的社会理想又重新鼓舞他们离开文学创作,转而写作反思社会历史、反思民族弱点的战斗性杂文,在无情的批判与自我批判中成为当代中国良知的代表。但是巴金与鲁迅相比,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鲁迅在社会理想方面持现实的战斗态度,他渴望与先锋性的社会思潮结成同盟,从他者的理想中寻求未来道路;而巴金很早就接受并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自以为是接受了先进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因此对于别的社会思潮更多的是持批判态度。在1949年中国政治史上试图拉开社会主义的序幕时,他曾经努力从中找到与自己所期盼的理想世界相吻合的地方,所以在50年代他写作许多欢欣鼓舞的文章,也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并非全是虚情假意的话。正如他所崇拜的克鲁泡特金、柏克曼等人在十月革命后也都满腔热忱地回到俄罗斯去参加理想世界的建设一样,一个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绝不可能无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标题是“我是来学习的”,这句话正是柏克曼当年回到俄罗斯在群众欢迎大会上的发言题目。我想当时的巴金一定会想到克鲁泡特金等人在俄罗斯的遭遇和事迹。克鲁泡特金晚年隐居在莫斯科的郊外别墅里,埋头写作皇皇巨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为的是他觉得无产阶级掌握了革命政权以后,更应该关注精神道德的建设和善良人性的培养。巴金深受克氏的影响,这才有了他在“文革”浩劫以后的《随想录》的写作,这也是巴金的伦理学和道德完善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他与鲁迅去世时怀着对旧世界的怨毒,喊着“一个也不宽恕”的悲愤咒语有所不同。鲁迅绝望而战斗,无比深刻;巴金则始终有理想的照耀,他的绝望中有温情,多少是含有遗憾惋惜的因素。
《随想录》是中国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述,事实上也只有巴金才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这是巴金学习鲁迅的最后一次重大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