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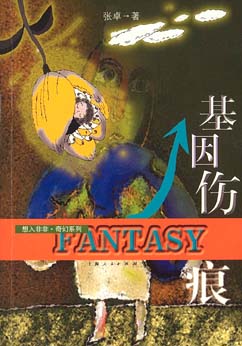 在QQ上碰到朋友,问:最近在看什么书?答:几米喽,不知道的话被人唤作麻瓜啊。 在QQ上碰到朋友,问:最近在看什么书?答:几米喽,不知道的话被人唤作麻瓜啊。
什么麻瓜?
哈利·波特式的语言啊。这也不知道,够麻瓜哦J。
我笑,社会有向卡通化发展的趋向啊。你看,都市人都在看哈利·波特,都在看几米绘画本。那个骑着飞天扫帚的小男孩不仅带着孩子的梦想还让成年人的天空变得异常灿烂。童话不再只是书城的儿童专柜所有,它上了排行榜成了畅销书渐渐演变成一种时尚。
我也爱看几米的作品,那些单纯的,细碎的不经意的小感觉好像已经被我们淡忘,但几米用画用文字重新把它们从心底唤出来,让时过境迁的我们重新体会那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让我们在感动之余多了份淡淡的忧伤,让我们从童趣中读出了诗意与哲理。
相对于几米的沧桑,几个年轻人创作的带有魔怪、魔法、幻想、童话、传说等等因素的小说则让人感到新奇与跳跃。继《哈利·波特》、《魔戒》、《鸡皮疙瘩丛书》之后,鉴于“洋奇幻称霸,土产品尴尬” 的局面,上海人民出版社策划了一套想入非非丛书,倡导本土的、原创的、适合中国国情且具有时代感的系列读物。“想入非非”第一辑收录了陈洁、周末、张卓、刘相辉的作品,即《精灵诺儿》、《突然消失》、《基因伤痕》、《撒旦的玩偶》。是追赶潮流,是童心未泯,还是天生爱幻想?年轻的作者是怎样来看待童话的?
作为责任编辑之一,我在“想入非非”第二辑的约稿过程中与《琉璃沙》的作者张雯婧谈起了这个话题。于是有了如下的自述性文字:
《琉璃沙》写于两年以后,其间经历了高考。我一直以为一个人的心智会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或阅历的丰富逐渐成熟起来,我也想从我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的成长历程。而当《琉璃沙》完稿之时,我竟意外地发觉这篇小说中居然还会有关于“王子”的幻想。于是我便笑自己,我是否打算一生写童话呢?师长们毫无疑问是不支持我写一些在他们眼中极为幼稚而不合逻辑的东西的,他们认为我长期沉溺在“空想主义”里,会不自觉地把文风练小气了,我从小到大参加作文竞赛无数却没有一次拿奖,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他们会鼓励我说,出去走走,观察观察社会现象,写点务实的文章。似乎只有写点务实的文章,才会有奔头。
对此,我不屑一顾。
但是我偶尔也会想,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不再把写作仅仅视为一种乐趣,我只惦记着投投稿呀换面包呀,那时候再回头看看当下的自己,会不会也觉得可笑呢?如果大多数人的幻想最终都敌不过现实的无奈,我但愿自己能成为那一小部分中的让心灵永远居住在不可触及的彼岸的人。即使有那么一天,当彼岸不得不变成此岸,我也希望别来得太快。
创作《琉璃沙》这个故事的灵感起初来源于三毛。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某一天能如三毛那样做一个流浪的歌者,披星戴月,餐风宿露,踏遍撒哈拉的每一寸土地,寻找一种传说中的奇异的沙子。后来读了采访三毛的笔录才知道,只有那些从没有流浪过的人才会把流浪想象成潇洒和浪漫的生活。艰辛的旅途远非文字所能矫饰。现实毕竟并不唯美,唯美只存在于人们的初衷。所以,我的故事里没有流浪。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在既定的事实上期待奇迹的发生,而不是在完全没有作好遭遇挫折的心理准备时,对着一份难能可贵的幸福吹毛求疵,因它的遥远而为自己的不执着找来种种借口,以过程的悲哀来逼迫自己放弃追寻的信念。
我喜欢童话里的爱情,喜欢童话里虚无缥渺的东西。当梦与现实起冲撞的时候,我只要拿一支笔,便可以实现它们之间最完美的结合。这让我感到无比欢愉。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当爱情追求实质,爱情就像影子般飞逝。追,追,追那飞逝的;飞,飞,飞离那追逐的。”或许有很多人承受不起时间的考验,使尚未涉世的人也开始怀疑幸福的有无。当一种爱情来得太偶然或太趋向于完美,我们就觉得它像童话,而童话又是最经不起向下猜测的,所以爱情就不可信。我们宁愿选择更可靠的生活,年年岁岁,过着怨天尤人的日子,让圆满在碰触指间的那一刻悄悄流向彼岸。生命不该有如此负荷。我们自以为是地把一切都看透彻了、想透彻了,我们忽略的是什么呢,在繁华的浮躁的都市里,来不及体验生活的情趣,不懂得怎样营造氛围,忘却了去捕捉眼神交会时的瞬间的感动,而那仅仅在一念之间的,往往就是生命最本原的美丽。
所以我觉得应该写些什么,来挽留人们心目中那份渐渐被遗落的纯真。
是的,挽留纯真,其实奇幻小说的热销,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需求。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的生存压力比较大,而奇幻小说以架空当世的样式,对人们的心理重负起到了缓解作用。
那么,作为一个不再是孩子的成人读者,你喜欢童话的理由是什么?看了陈洁的《精灵诺儿》有个叫陈近朱的大朋友在网上留下了这些文字:
如果你把《精灵诺儿》叫作儿童文学、童话或者是幻想文学我想都是可以的,反正对于我这样一个早就过了20岁生日的人来说看这样的东西依然如同走在阳春三月的河畔,让毛茸茸的柳絮钻进心眼一样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