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真人秀作为娱乐消费文化和大众媒介“联姻”的一种典型样本,无疑随时可能出现在任何人群中的“茶余饭后”。无论是“窥探”“猎奇”明星生活,看他们社交关系的极限拉扯、情商角力,还是追求心理陪伴与补偿,通过消费这一文化产品获得身份认同和自我实现,电视真人秀都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以戏剧化的视角观察社会、生活与人生的机会,观众所见的,不仅是一群人的“狂欢”,也是“镜中的自己”。下文选自《“玻璃屋”里的纷争——电视真人秀中的戏剧性》,针对电视真人秀的“人文科学实验性”展开了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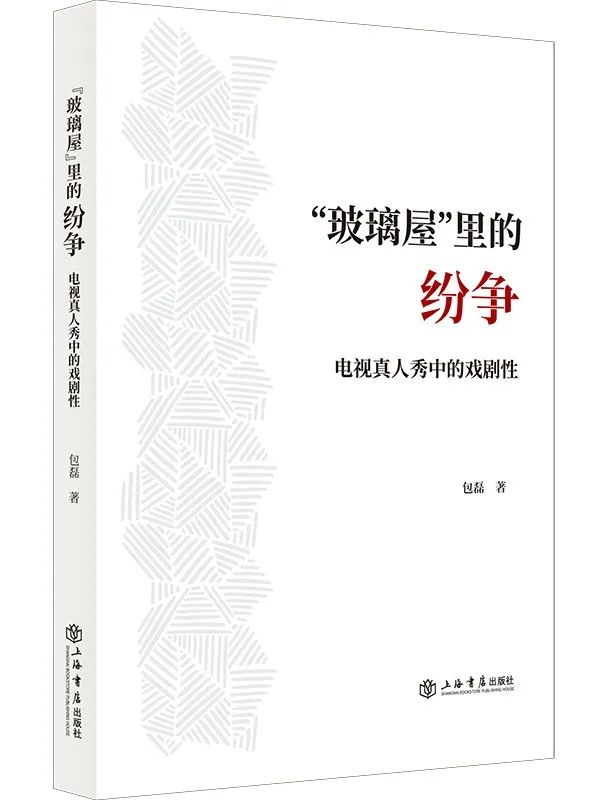
《“玻璃屋”里的纷争:电视真人秀中的戏剧性》
包磊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电视真人秀自20世纪诞生以来不断引发收视高潮,这不仅展示了米歇尔·福柯笔下文明的“疯癫”,也将人类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当人们跳出自己身处的社会维度,以一种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观看真人秀节目时,正符合实验室内研究者观察实验样本的姿态。这种视角与福柯、布尔迪厄、阿多诺等社会学者对于电视等大众媒体的“祛魅”和反思相契合,显示为一种科学研究的“观察态”。相对而言,人们在设计或参与这些真人秀时,则接近于一种工作及生活上的“游戏态”。以上二者共同完成了人类社会及行为可观察、可复现的拟态试验。可以说,作为文化工业产物的电视真人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镜像游戏”。
以“游戏”为主要形态的电视真人秀,无论是益智问答、才艺竞技、工艺制作、相亲交友还是旅游冒险、学徒养成等何种表象,不变的是优胜劣汰的实境真人游戏。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曾将游戏的表现形式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它是一种脱离常规生活的假定或假装行为;其次,这种假定性的活动所依据的规则是自规定性的,即由游戏共同体自己制定,无需得到他人认同。”[1]这与戏剧的假定性在真人秀中的应用又如出一辙:现代人有时愿意放弃一定的自由,是因为更多的自由伴随着更多的责任,而对于社会生活的虚拟让人可以逃避这些责任。
在这种不必负责的“游戏态”下,长期生活在规则之下的人们获得了一种“自由”,并不用为之付出现实代价,即能产生一种快感和满足,消解现代社会中的压抑和单调。这种游戏态产生的效果与戏剧活动所带来的纾解压力、获得审美、引人思考十分接近。可以说,真人秀的参与者们所追求的不仅是丰厚的物质奖励,也有合法地“游戏人生”的诱惑。
事实上,每一种媒体的出现和普及都会带来大众文化形式的更新以及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网络时代,人与人最远的距离不是飞行的里程,而是面对面相对无言各自处理自己的社交信息。真人秀所带来的在真实时空中“游戏人生”的体验方式,是社会大众积极自我表达,尝试改变生活状态的一种努力,也是雅克·拉康笔下以游戏互动寻找“自我”的一种“镜像”。
以导演《极限挑战》闻名业界的严敏在接受《智族GQ》杂志的采访时曾提出,他理解的真人秀之所以被称为“国民综艺”,至少缘于三层含义:第一层,它是全体国民、全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欣赏消费的内容;第二层,它能真实反映国民在现实生活当中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第三层,始终和全体国民站在一起。这个“三层论”也可以总结为娱乐消费、反映生活和揭示生活三个层面。也就是说,当观众在观看或者参与优秀的真人秀节目的时候,首先吸引他们的是“有趣”“好玩”这些浅层的娱乐性;让他们产生“欲罢不能”的感觉的,是戏剧性所带来的对于人物命运及事件发展的持续关注,并且多多少少会引起他们的思考——“To be or not to be”。但让观众真正产生认同感的,一定是节目对现实的映射和反思,而要产生这种效果,就离不开艺术以外学科的介入和应用。他认为:“我们长久把它矮化为了第一层。”[2]
“矮化”的原因,涉及编导人员的业务水准以及文化思想水平的局限。从戏剧的角度来看,电视节目由于其结局基本上为“皆大欢喜”,很容易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喜剧”。“对于不能免俗的真人秀而言,只有设置得当的游戏流程,才能在喜剧式的结局中使观众认识到娱乐表面之下的悲剧性。而悲剧往往具有强大的批判精神,因为在悲剧中,人的反抗总是以他的殉难或失败告终,这就对那些导致悲剧英雄毁灭或失败的根源构成强烈的怀疑和否定,从而达到批判效果。”[3]纪录片之所以易于为知识分子所接受,也部分地缘于它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真人秀本身的戏剧性已经具备了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反映社会现象的功能,在记录方式上又继承了纪录片的部分元素,如果停留在“逗人发笑”的层面上,便是一种创作上的“暴殄天物”了。正是在这种戏剧性设置必须依托社会科学层面的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认知的鸿沟”,最终造成作品的内涵深浅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