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只讨论自己最熟知的音乐——与文字相关联的音乐。我希望能够表明,由于它们与语言和文本的联系,在巴赫的康塔塔、经文歌、受难曲和弥撒曲这些不可超越的作品中,存在着此前未曾有人尝试或者敢于表达,或说能够用声音表达的东西。
对我而言,从初次遇到这些作品,到这些年不断的排练与演出,我度过了心无旁骛的岁月,激动的火焰愈燃愈烈。这个丰盈、雄浑的世界,和作为一位指挥以及终生的巴赫门徒在其中领受的喜悦,正是我最想传达的。
——约翰·艾略特·加德纳
《天堂城堡中的音乐:巴赫传》
[英]约翰·艾略特·加德纳 著
王隽妮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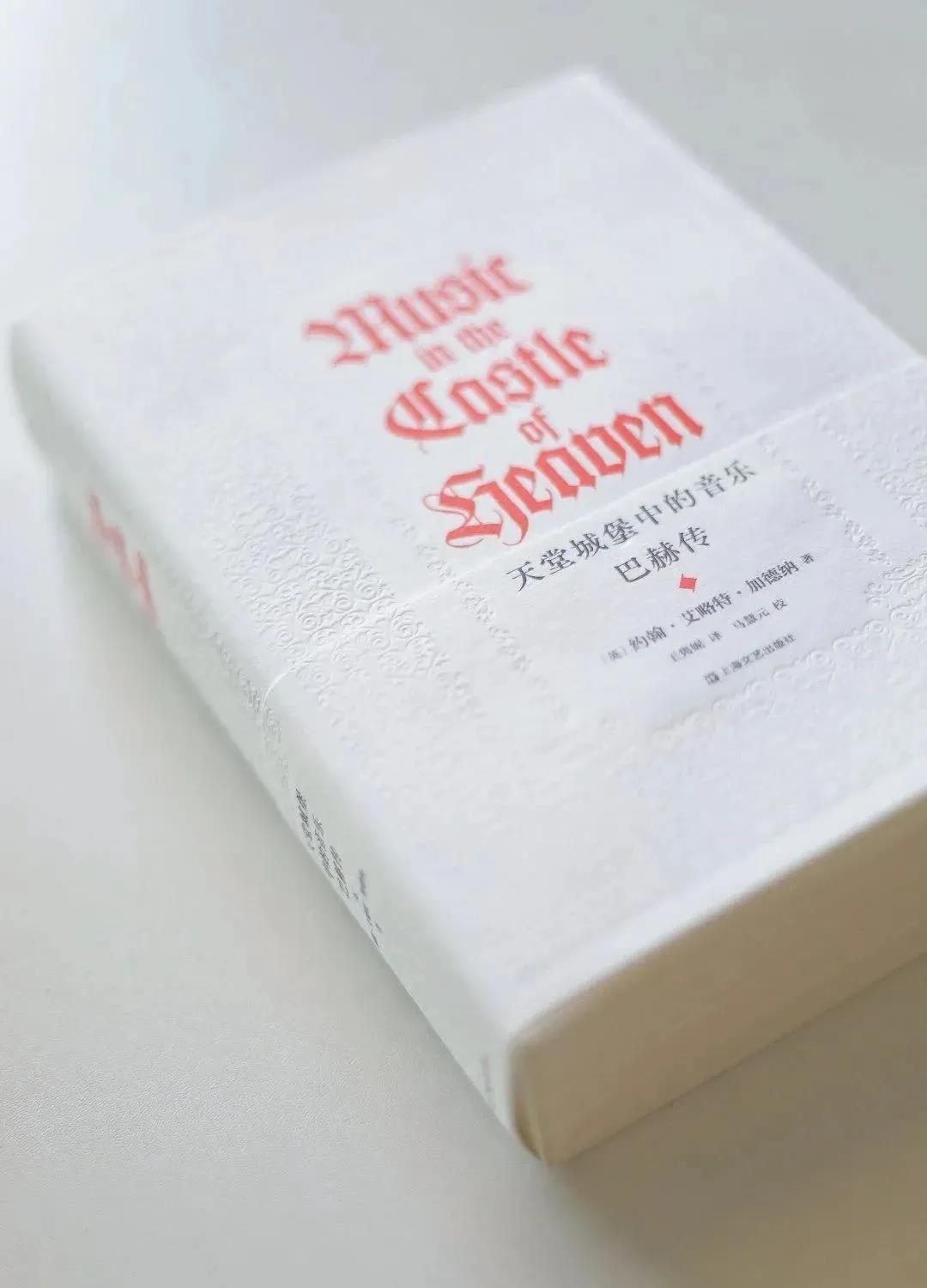
我越发觉得,可能许多被巴赫震撼和眩惑的作者,依然默认巴赫极大的天赋与他个人的境界有着直接关联——这令人不安。他们会因此对他的缺点异常容忍,这些缺点有目共睹:易怒、乖张、自大,羞于接受智性的挑战,对于皇室成员和政府,他既有怀疑,也同时为自己谋利。
然而为何要认定伟大的音乐源自伟大的人呢?音乐能够启示和提升我们,但未必是因为创作者善于启发别人(创作者只是自己受到了启发)。在某些情况下,也许会有这样的联系,但这并非唯一可能。也许,“讲故事的人相比故事本身,或者无足轻重,或者缺乏吸引力”。
巴赫的作品是由伟大心灵的卓越才华构成,但这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探寻其人格的直接线索。事实上,对某事物的了解,可能会引致对另一事物的认知错位。至少他绝不会像许多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我能立刻想到的有拜伦、柏辽兹和海涅)那样被我们过度挖掘,或像瓦格纳那样,被推断出创造力与病态之间令人不适的关联。
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美化巴赫的形象,也没有必要无视可能存在的阴暗面。
一些新近的传记试图对他的人格乐观想象,从积极的角度诠释一切,而这点也已经被现存的原始资料拆穿。
巴赫这一生与其说是孜孜不倦地用功,不如说是一直对智识上不如自己的人摧眉折腰,这可能会对他思想状态和幸福安宁带来心理负担,却被这些作者低估了。任何加之于巴赫的近乎于神的形象,都蒙蔽了我们的双眼:看不见他艺术上的艰难探索,也渐渐不再将他视作出类拔萃的音乐匠人。正如我们习惯于将勃拉姆斯看成一个蓄须的发福老人,忘记了他曾经年轻又风度翩翩——如同舒曼在他们首次会面后所描述的“来自北方的幼鹰”。
同样,我们印象中的巴赫,是个德国宫廷老乐长,头戴假发,长着双下巴,这一形象又被投射到他的音乐上,尽管他的音乐经常洋溢着朝气和无比丰沛的活力。假定我们换一种思路,把他看成不那么讨喜的反叛者:“他破坏(音乐上)广受赞誉的原则,瓦解严密守护的观念”。对于这一观点,劳伦斯·德雷福斯(Laurence Dreyfus)非常赞同,他指出:“因为它允许我们怀抱早期的敬畏感,那种我们很多人一听到巴赫作品就产生的感觉,并将其转化成对作曲家勇气和胆识的想象,从而让我们对他的音乐有新的体验……
作为一个站在声乐与器乐合奏组前的演奏者和指挥,我试图表达从这种位置接近巴赫的感受,正如他自己也习惯站在这一位置。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立足点,由此得到的任何“证据”都会轻易被驳斥为主观和站不住脚的,它只是“音乐即自传这种浪漫想法的又一新论”,且以“不可能的权威”为推测背书。
相信在音乐唤起的情感的影响下,作曲家的意图能够被捕捉,这当然是一种诱人的想法——虽然事实可能根本不是这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性本身与更为客观的事实相悖,或者会毁坏其结论。
也许除了那些数学上的真理,一切真理在根本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主观性。
过去的巴赫研究常是主体(作者)和客体(作曲家)相疏离,有时候主体甚至被移除。然而,一旦作者的主观性几近抹除,或者不被承认,就会造成探寻巴赫人格多面性之路的封塞。在序言里,我解释了我个人独特的主观性的背景与属性。如果我因此激励他人去分析自己对巴赫的主观回应,并且去细思这种回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他的感知,我希望这种做法能够得到谅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