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美国人,在吉林市附近的荒地村住下来,当着东北人的女婿和当地学校英语老师,在实实在在的他乡异地,写了一部正儿八经的“返乡日记”。竟然连写作初衷都与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分相似——因为警惕于农村凋零和农村话语长期缺失,而亲身匍匐于田埂乡野,试图以小见大、抚今追古,对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一探究竟。
“因为我想要读关于中国农村变迁的书,所以我搬到了乡下,通过调研写就了《东北游记》(In Manchuria: A Village Called Wastelan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梅英东(Michael Meyer)说。作为一位1995年即作为早期“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前往四川支教的美国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出版自己的中国见闻。
2008年,梅英东根据自己在北京胡同的居住经历出版了《再会,老北京》(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一书,还原了他在北京奥运会前亲历的胡同拆迁对居民和城市文化的影响,展现了隐藏在北京城市发展叙事下的另一番图景。一位豆瓣网友是这样评价《再会,老北京》这本书的——“好多来龙去脉和前世今生,好多‘近在眼前’和‘远在天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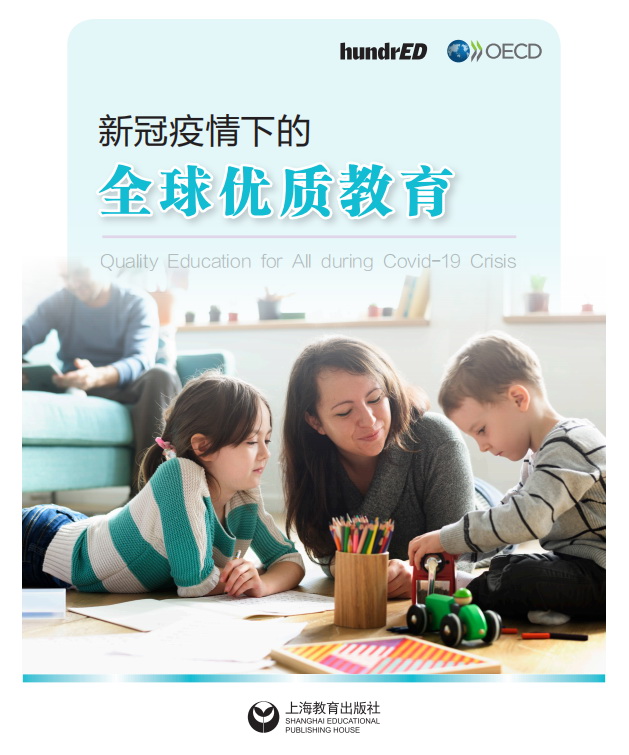
在《东北游记》中,梅英东写到了在北京生活时自己心中隐隐约约的疑问:“在现代中国的故事中,主角是首都和沿海城市。看那些闪闪发光的城市!那些新城!那些主办奥运会的城市!那些拥挤不堪、阶级分明、过分拥挤的城市!大多数外国驻华记者都居住在城市,中国的作家也一直将写作重心放在都市生活和城市知识分子上。”
这成了他踏上东北之旅的开端。
当这样一位“文化局外人”来到现场书写中国农村,他似乎享受着一些天然的优势,比如不落窠臼、饶有兴致地发现一些生活日常中的趣味。纵然是美国人,作为东北人女婿的他也逃不掉诸如三姑六婆催着生娃的尴尬桥段,但这种冒犯常常消弭于他的幽默和自嘲中。这个如条件反射般用“一米八六、属鼠”介绍自己的美国人,始终抱着外来者的天然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而他笔下的那些东北人,在各个节气间流转,在时代浪潮中翻滚,却依然拥有一种难得的真实的力量。
除了描写他的个人际遇以外,梅英东还叙述了他游历东北各地的经历,追溯了这块土地的复杂历史。当可见的历史只存在于亲历者的脑海中时,他用更大的耐心去回顾这片土地的前世,试图将之与当下连接起来。当他在大连日本军部旧址抚摸伪满洲国地图时,脑海中闪过的一幕幕历史画面貌似和此时此刻并无关系,却又流露出一种吊诡的宿命感。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时,梅英东说:“在中国,历史无所不在,但通常它是一道鬼魅般的痕迹,或是一种透明般的存在。你需要用一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
对于他来说,无论是被称作“满洲”还是“东北”,这片土地都是一个一半存在于现实、一半存在于想象的地方。而描绘出位于这两者之间的真实,则是他书写中国的终极目标。
专访《东北游记》作者梅英东
界面文化:你是怎样想到写一本关于东北的书的?
梅英东:当我发现我想读的书不存在时,我就知道,是时候写一本出来了。我想要读关于北京在变化过程中失去了什么的书,所以我写了《再会,老北京》。同样地,因为我想要读关于中国农村变迁的书,所以我搬到了乡下,调研写就了《东北游记》。
我还想借此机会写一写中国的一个地区。大多数关于这个国家的书籍和报道,都把它描述得好像只有一种单一文化,但事实上,这个国家就像美国或欧洲那样,在地理上、文化上和历史上有着千差万别。而且,它非常美。
界面文化:在书中你写道:“我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城市变迁的东西,而现在关心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你还注意到了中国的农村话语一直被城市话语所掩盖。这一观察是如何影响你的写作的?近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公众实际上对这个现象有诸多讨论,这也直接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返乡日记”的出版。许多学者和记者返回乡下记录他们的观察,而他们的记录常常令城市读者感到惊诧。你是否认为《东北游记》是又一部“返乡日记”呢?
梅英东:就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以算是,因为我选择搬到了位于吉林市附近的我妻子老家所在的村庄,在那里人们耕种有机大米。但很快我意识到,书写农村比书写城市要困难得多:当地政府办公室没有任何过去的税收或人口普查记录,这附近一带也完全没有历史遗存。除了描述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差异之外,作者还需要深入挖掘中国的历史。许多历史如今只存在于亲历者们的脑海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