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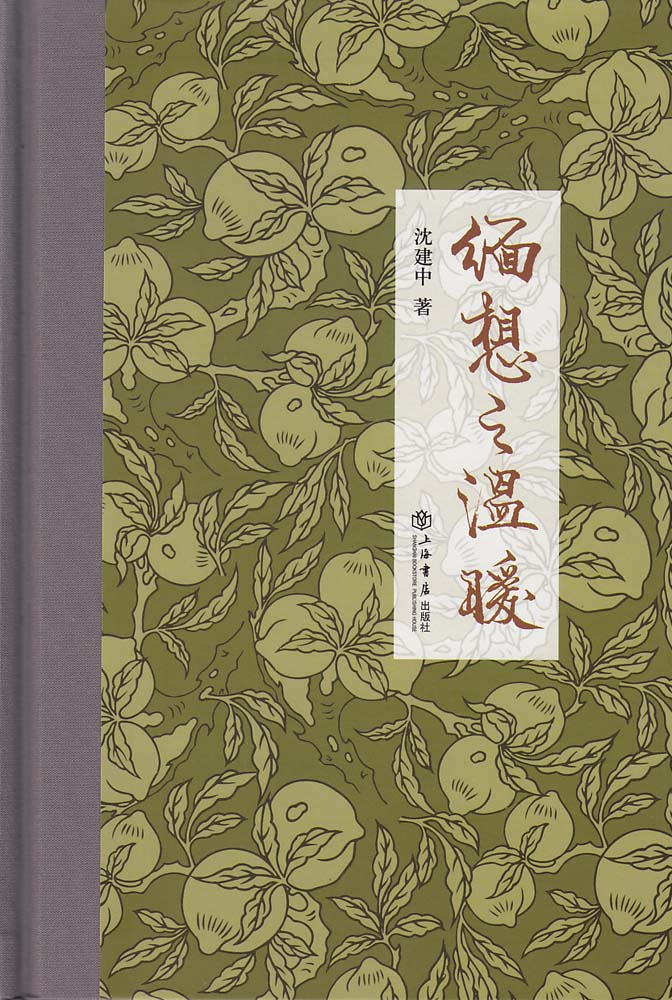 大约有一年了,那时忽然流行一首歌,引起“时间都去哪儿了”的议论,读着各式各样的闲闲讲述,让我不禁反省自我时间跑到哪儿去,究竟做些甚么,是如何耗费的。遂沉湎于想念过去光阴似水流之种种情形,感觉是有几许暖意融融。 大约有一年了,那时忽然流行一首歌,引起“时间都去哪儿了”的议论,读着各式各样的闲闲讲述,让我不禁反省自我时间跑到哪儿去,究竟做些甚么,是如何耗费的。遂沉湎于想念过去光阴似水流之种种情形,感觉是有几许暖意融融。
大约素来衣着略少,常常想着能够汲取一些温暖。其实,我并不惮寒冷,哪怕腊月里,也不。1990年代中期曾有一年隆冬,冒寒北上天津逛旧货地摊,北风凛冽,冻冷彻骨,扛不住的摊位跑了许多,而我身着单衣,居然擦着鼻涕跟留守摊位的主儿调侃。今天想来也够得上自作自受似的锻炼吧。可我却偏偏不堪夏季高温楼里空调骤降温度,奇怪!一旦风口齐吹,冷峭袭来,寒战顿起,明明是“寒症”伤风还吃了“热症”感冒之败火凉药,寒上添凉。怪谁呢?
如今已少有“纳凉”一说,盛夏只要躲在空调房间里便“万事大吉”,犹如宋人苏轼吟诗“遥想纳凉清夜永,窗前微月照汪汪”那般,目下我只能真实地“遥想”纳凉了。但小时候实在享受过杨万里诗句里“大人摇蒲扇,小儿捉蜻蜓;树上蝉自鸣,随你听不听”的那份悠然纳凉光景。年齿渐长,免不了沾染“老的总归好”之癖习,故最爱惜廿年之前发给我的工作西服,现存那套早已胸前起皱、袖口磨损,却穿得舒服自在,那面料尤其厚实,已是我很多年来过冬的外套。
其实,在走过一天天的日脚里,除了几位不断给予我暖意的要好同事外,更应忍耐的是大热天空调所带来的后遗症。沈从文先生如是说:“在寂寞里我也自慰过,‘还是春天,无望无助地做点事情,把自己放在一个沉默里过日子,抓到这寂寞,再来作新的迈步。什么是将来,可以不必过问,不用打算。’可是到了连昨日做的事也不能保留到记忆上,我觉得工作的无聊可怜了。”因为曾有苦不堪言的伤风着凉教训,平常一有机会便设法保暖。好在胡思乱想地忆念过去,成了现下的不二法门。
有一种颇似真理的说法:“时间就是金钱。”那么,金钱也可否换得时间呢?当然,若不需要拼命挣养家糊口之外更多的钞票,大概能给自我留出一些富余时间。依小时候学校晨跑高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这些年慢慢地体会到我那几位要好同事好像是天天在默念“一不怕苦、二不怕钱”的豪言壮语过日脚,工余总是潜心练字,又不至于如《书谱》中说到“五乖”之“心遗体留”“意违势屈”,皆是心平气和地戒除贪性,力求把字写得横平竖直,规规矩矩,好像从前贾植芳老人说的那样——“把人字写得端正”。在我看来,他们就是这么幸福地打发时间的,好像有点倔、有点傻。不过,我确实从中体味到蕴藉生活的“真”“善”,如今我也希望自己能保持些许倔与傻,似乎有些惬意的,还能享受过“美”的日脚。可见其道不孤。
而今想一想自己以往时日,基本上都是跟着要好同事后面练字度过的。且要听乐,甚至喝茶,花费了较多时间,曾拟议练字听“巴赫”,喝茶听“海顿”。但从前也喜欢骑着只有铃声不响的咣当咣当的自行车,听着“莫扎特”信步游,居然用了十年业余时间拍摄照片;那时又在暗房里听着“贝多芬”竟然留存了五万余张底片。近年来再用相当时间将底片一一扫描录入电脑,包括整理、编目和刻盘诸事。粗粗计算一下,每天平均需要扫描十来张底片,方能在十年内完成。工余这般忙碌,让我特别吝啬时间,当面对电脑显示器,看着早已逝去的光影情景,心里尚存热情,时光仿佛倒流。如斯如斯,总之约摸二十年时间就这样最终留存于容量2T的两只移动硬盘里。每次翻看缅怀,亦倍感心跳加快,浑身暖热。
现在我已经习惯这样温暖的缅想,而时常想入非非,或许会“跑野马”,说不定能钻出一个甚么样的古怪念头来。某日觉得疲累而无所事事,忽然打量起一叠泛黄的报刊,都是积累的“鄙作拙文”获准被刊登的存样,犹如以往一页页练字的毛边纸,无疑又让我陷入过去的日日夜夜,每每极力避免写成歪歪斜斜,于是就坐姿端正挺直。今天想来难免感慨。恰恰昨前两个晚上正在阅读周毅君的书,一本书名曰《过去心》,很是禅意,我觉得好像也在小结“时间都去哪儿了”;另一本书更直白地题名为《往前走,往后看》,这不就如同我在平日里遣闷的“缅想”过程么,都是尤其难得的细腻素描。
由此启发,我竟然决计仿照她那样也把以前的文章拢在一起,发觉基本上是为报刊和编书而写,虽说有些偶然性,可都是自己走过的一个个青涩足印,很是稚弱。但也有情绪寄托在,也有心理踪迹在。当然可以说,我过去的时间仿佛都在这儿了。
值此成书之际,谨感谢时间,感谢缅想,感谢温暖——哦,无可讳言,是由衷的。
甲午十一月大寒前五日于谦约居北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