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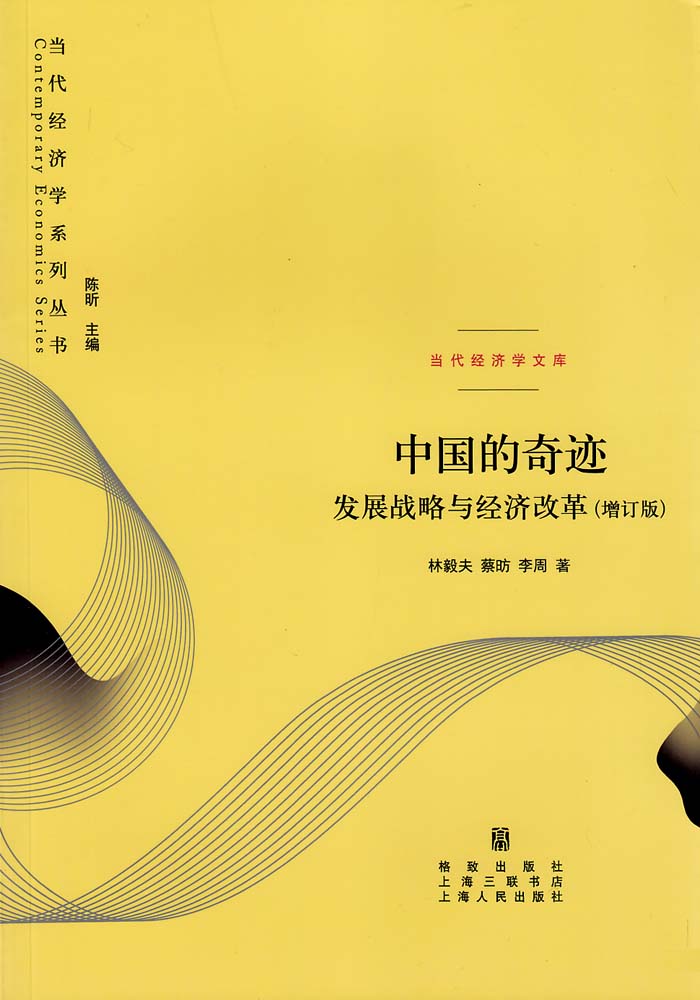 最早知道林毅夫这个名字,大约是在1988年。那时我在上海三联书店任总编辑,记得有一次去北京组稿,见到上海老乡周其仁,他告诉我:他所在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新来了位副所长,叫林毅夫,刚从美国学成回国,在美期间曾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又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此人受过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有机会你可以向他组稿”。那时我正在策划主编“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这套书的宗旨是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试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从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的角度看,林毅夫当然是这套丛书最理想也是最紧缺的作者。于是,利用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我找到了林毅夫,向他介绍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的情况,并提出了约稿的请求。记得当时林毅夫很坦率地告诉我,目前他的研究领域在中国农业发展方面,但研究成果还未达到出版专著的程度,他还说一旦研究成果成熟,会找我商谈编辑出版事宜的。 最早知道林毅夫这个名字,大约是在1988年。那时我在上海三联书店任总编辑,记得有一次去北京组稿,见到上海老乡周其仁,他告诉我:他所在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新来了位副所长,叫林毅夫,刚从美国学成回国,在美期间曾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又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此人受过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有机会你可以向他组稿”。那时我正在策划主编“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这套书的宗旨是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试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从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的角度看,林毅夫当然是这套丛书最理想也是最紧缺的作者。于是,利用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我找到了林毅夫,向他介绍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的情况,并提出了约稿的请求。记得当时林毅夫很坦率地告诉我,目前他的研究领域在中国农业发展方面,但研究成果还未达到出版专著的程度,他还说一旦研究成果成熟,会找我商谈编辑出版事宜的。
从那以后,林毅夫的研究进展情况一直在我的牵挂之中。1991年初我去香港工作,担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的总编辑。那一年的夏天,林毅夫出访美国途经香港,打电话约我见面。到他下榻的酒店后,看到在座的还有他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学长王于渐先生,王于渐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后来担任了香港大学的副校长。林毅夫把王于渐与我约到一起,一个目的是为了介绍我们相识,帮我在香港打开学界的局面。这次见面,林毅夫向我介绍了他的研究工作,目前主要精力已放在研究中国的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前一阶段他关于中国农业发展与改革的研究有了成系列的成果,约有十来篇论文,并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结集出版。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喜讯,在这之前,我已经知道他关于中国农业发展与改革的多篇论文刊发在国际一流经济学杂志上,并备受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我们约定将这部书稿放在“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1991年年底,林毅夫将书稿寄至香港,那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在宿舍里做的功课就是编辑这部名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著作。这部著作集中了林毅夫最初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10篇论文大多是关于中国农业发展和改革的经验实证分析,侧重于制度和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变迁的原因。这本书当然是中国经济学当时最具国际规范的研究成果。但是,令我更感兴趣的是,书中所收的最后一篇题为《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的论文,它使我对林毅夫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写到,除了最近的二或三个世纪之外,历史上中国在绝大多数主要的科学技术领域一直大大领先于西方世界。历史学家一般都承认,到14世纪,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具备了发生工业革命的几乎所有主要条件。但是,中国却没有再向前迈进,因此当18世纪中后期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后,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李约瑟将这样一个矛盾归纳为如下具有挑战性的两难问题:第一,为什么历史上中国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其他文明?第二,为什么到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不再领先于其他文明?对于这样一个难题,历史学家、科技史专家都曾做出过不同的解释。作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居然也对这个难题感兴趣,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在这篇论文中,林毅夫不仅评述了前人的假说,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供给不足假说,并做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解释。我对林毅夫的全新认识主要在于,从这篇论文中我知道早在中学时代他就有强烈的报效民族和国家的愿望,后来从事经济学研究也是为了探索中国富强之路。他曾多次说过,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完全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样的话,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经历了由盛到衰,再由衰到盛的大国”,拳拳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其实,细心的人们从林毅夫一系列著作和演讲中都可以读到他始终如一的报国之情。
跳出中国农业发展和改革的领域,在更广的范围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据林毅夫自己说是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中国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高层和经济学家纷纷讨论通货膨胀的起因、形成机理和治理对策。林毅夫和蔡昉、李周一起参加到“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困境”的课题研究中,试图解释中国传统计划体制的形成逻辑、改革中出现的“活乱”循环和旷日持久的难点问题,提出解决难题的改革路径和战略。他们三位的这项研究长达五六年之久,最终的成果就是他们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1994年初,林毅夫将书稿交我,希望放入“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