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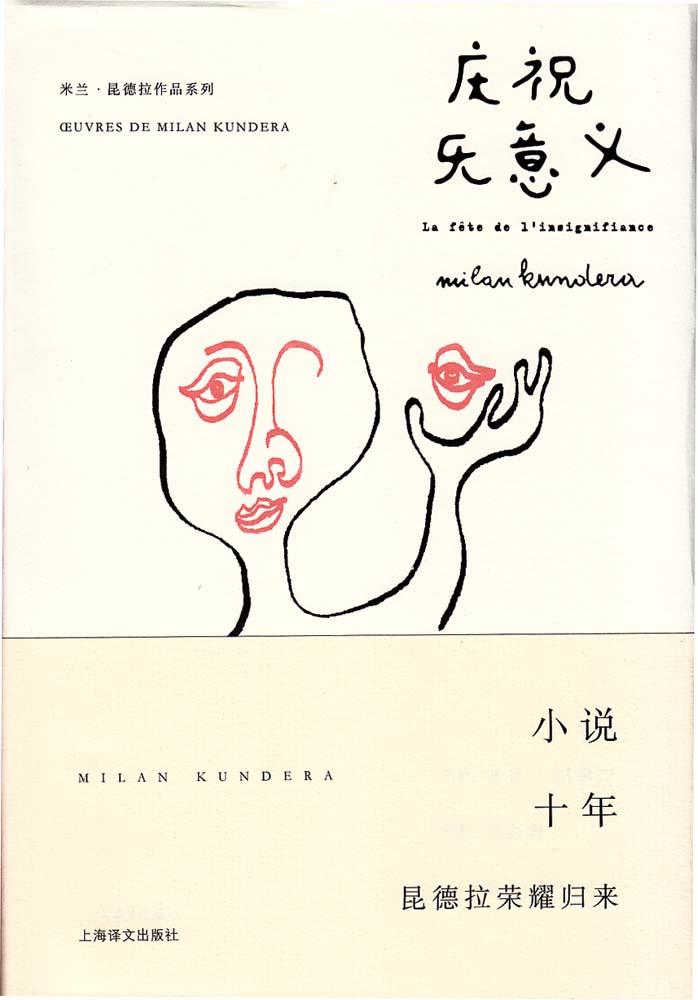 无须把米兰·昆德拉的过往名作作为背景渲染,一部小说本来就应是一个独立的文本,即便作者有意将多部作品情节进行串联,也不应影响对一部作品的基本判断。所以,本书故事理应成为我们“解码”的首要依托载体。小说从阿兰、拉蒙、夏尔、凯列班四个好朋友入手,顺着他们的脚步、他们的生活故事、他们三三两两的谈话,引出了巴黎街头的花季少女,市民热捧的夏加尔画展,斯大林二十四只鹧鸪的玩笑,尿急的苏维埃傀儡主席,自杀未遂却杀人的母亲,以及天堂纷纷坠落的天使…… 无须把米兰·昆德拉的过往名作作为背景渲染,一部小说本来就应是一个独立的文本,即便作者有意将多部作品情节进行串联,也不应影响对一部作品的基本判断。所以,本书故事理应成为我们“解码”的首要依托载体。小说从阿兰、拉蒙、夏尔、凯列班四个好朋友入手,顺着他们的脚步、他们的生活故事、他们三三两两的谈话,引出了巴黎街头的花季少女,市民热捧的夏加尔画展,斯大林二十四只鹧鸪的玩笑,尿急的苏维埃傀儡主席,自杀未遂却杀人的母亲,以及天堂纷纷坠落的天使……
在这个被隐喻为“木偶”剧的鸡尾酒会上,装模作样的主人客人纷纷将内心掩盖得结结实实——浮华、尊贵且见不到一丝本真,尽情表演成了这里最大的秀场。倒是那位葡萄牙女佣——玛丽亚娜天真地以为凯列班真就来自巴基斯坦,至而推心置腹,至而对表面看似真诚的凯列班心生爱意。凯列班将玛丽亚娜比作天使,实暗喻这种温暖关系将会很快走到终点,错不在天使,而在于他并非真正来自巴基斯坦,晚会上的那一切,只是曾跑过龙套的他略施的伎俩。
除了鸡尾酒会,另有两个故事相对深刻,即二十四只鹧鸪和自杀未遂却杀人的母亲。前面一个是极权者卖弄权术的灰色幽默,很容易令国内读者想到这么一句话: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极权者总是渴望拥有一双偷窥他人内心的眼睛,总是渴望有一种神奇的理论掌控他人思维。后一个故事是对生与死的反思,一个看起来视死如归的人,最后关头在内心本能的呼唤下保住了性命,而那个见义勇为者却被拖入了水下。所谓不怕死,往往先是不怕别人死,其次才是自己。
思考社会亦思考人生,这便是真的米兰·昆德拉。在社会角度方面,昆德拉通过对极权的诙谐描写,勾勒出一幕幕极权者个人导演且自以为高明的丑剧,其实早就如皇帝的新装,在权力的威慑下,没有人敢指出丑剧质量之低劣。而一旦涌现出“天真的小孩”,迎接极权的将会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极权时代,一旦看似那么祥和,实际则如同鸡尾酒会的那幕木偶剧。一切看似十分完美,但“完美无缺的节目——根本是无用的”。在极权的震慑下,完美的背后,每个人不得不按照所谓的程序努力掩盖自己,时常得提防不远处是否有一个“秃顶的男人”在暗中监视自己。
擅长哲学思维写作的昆德拉不想把一本书写得太过枯燥,所以在大处着眼的同时,努力做到小处着手,即通过解构个体的生活,进一步阐释人生的内涵。四个好朋友的人生各不相同,甚至有许多不如意之处。他们每天的忙碌,就像是被一堆毫无意义的工作牵着鼻子。昆德拉显然不这么认为——“我们周围的无意义,它是智慧的钥匙,它是好心情的钥匙……”生活并不需要试图每时每刻去阐释其意义,平淡本就是生活的色调,苛求在意义中生活,最终往往会受制于意义价值所带来的重重困扰。
从社会深入到群体,再从群体延伸至个人,昆德拉的笔锋铿锵延伸,他想要的不只是对社会现象的解构,还想抵达普遍个体最真的心灵港湾。当达德洛的女儿在鸡尾酒会上见到仰慕已久的“名女人”拉弗朗克时,这位收获无数赞美并引诸多男性追逐的美丽女人却淡淡地“倾诉衷肠”,“人即是孤独”,“层层孤独包围的孤独”。表面的被追捧无法取代内心的孤独,作为“名女人”的拉弗朗克给小达德洛泼的这盆冷水,何尝不是满肚苦水难以盛下的一次澎湃决堤。
一切完美均没有意义,承认不完美才是人类文明进步和个人生活幸福的源泉。反之,越是自诩为完美者,其本身就不完美,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因为他总想把一切事物的意义人为拉高扩大。
顺便想提一下的是,作为大师的昆德拉擅长在写作中加入哲学思维,至而引发读者的深思,这是其优长所在。不过,故事性的欠缺想必会成为读者的阅读障碍。本书小故事讲得有滋味,大故事却过于平淡、零散,四位主人公几乎都看不到特别完整的故事情节,更别谈转折和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