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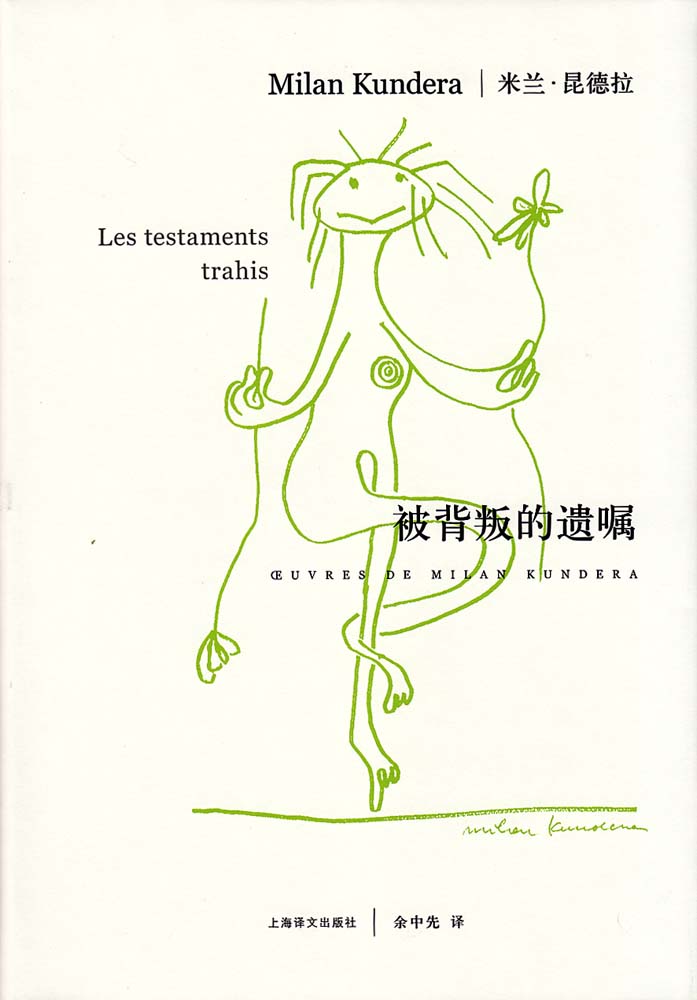 昆德拉最早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杨乐云在1977年第二期的《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了其编译的《美刊介绍捷克作家伐错立克和昆德拉》一文。之后,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在《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外国文学研究》1985 年第二期)一文中,重点介绍了马尔克斯和昆德拉这两位作家。1987年5、6 月间,作家出版社以“作家参考丛书”的方式,推出了韩少功和韩刚合译的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立即在中国文坛引起轰动,很快引发了所谓的“昆德拉热”。 昆德拉最早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杨乐云在1977年第二期的《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了其编译的《美刊介绍捷克作家伐错立克和昆德拉》一文。之后,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在《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外国文学研究》1985 年第二期)一文中,重点介绍了马尔克斯和昆德拉这两位作家。1987年5、6 月间,作家出版社以“作家参考丛书”的方式,推出了韩少功和韩刚合译的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立即在中国文坛引起轰动,很快引发了所谓的“昆德拉热”。
“东欧作家的思考不仅涉及到文学与社会本身,而且涉及到欧洲文学史、思想史及现代性诸问题,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颠覆了十八世纪后期浪漫主义思潮所建立起来的诸多基本文学观念,可称为一种批判的文学,这让我对东欧文学持续关注”,景凯旋说如是。
对于昆德拉来说,性爱与情欲是其“探讨人的本质的一个入口,是照亮人的本质的一束强光”。这种特有的主题及其叙述方式,恰好同时刺激了中国文学两根敏感的神经。他围绕“轻与重”、“肉体与灵魂”、“忠诚与背叛”、“记忆与遗忘”、“媚俗”、“玩笑”进行构思,他的讽刺、反讽,历尽辛酸之后的无奈、荒诞与自嘲,显得特别新颖,特别有力。
也许,后来广受青睐的“黑马作家”王小波在这一点上颇得昆德拉的神韵,他的“时代系列”中多少看到昆德拉的某种影子。王小波作品的个人气质也是反讽与诗意兼具的。他以反讽、幽默、荒诞、妙趣横生的文字,让一贯严肃拘谨的中国读者也有解放捆绑的轻松、痛快。王小波在《黄金时代》、《红拂夜奔》等小说中对历史中暴力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幕幕狂欢场面,充满了戏谑的反讽。和昆德拉相似,面对历史的荒谬,没有做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而是以黑色幽默解剖真相。王朔、韩少功作品都多多少少看得到昆德拉的原型和变异。
李欧梵:昆德拉写的是小人物 但运用的却是大手笔
昆德拉被正式介绍进中国,是在1985年。文学评论家李欧梵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了《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介绍了南美作家马尔克斯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以及他们各自的代表作。
“昆德拉写的是小人物,但运用的却是大手笔,不愧为世界文学的一位大家,足可与马尔克斯(1982年凭借《百年孤独》获诺贝尔文学奖)媲美。”李欧梵写道。他认为,昆德拉没能获奖的原因之一,是“政治煽动性大,也较年轻”。(以上节选自中国新闻周刊)
李欧梵还写过一篇文章评读米兰·昆德拉的《慢》的书评,以下是部分内容选摘:
流亡法国的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最近出版了一本小说,题目叫作《慢》。全书开始就说他和妻子在法国公路开车,有一辆车紧追其后拼命想超车,遂引起了他的一段哲学式的臆想:这个想超车的年轻人早已陷入一种速度的狂热之中,这种狂热的感觉几乎和人的身体无关,而纯是科技革命所造成的——一种由“纯速度本身”而得到的快感。
这种狂喜或快感并非快乐或乐趣,前者目的是速度上的高潮,愈快愈好,而后者却只能“慢慢”体会,所以昆德拉在书中又引用了一本18世纪的法国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如何在戏院邂逅到一个贵族妇人,她请他同车送她回家,由此而展开一段缠绵的偷情故事,这两个情人调情的节奏是慢的,而且更有情调,先在花园散步,散步到家门口的时又故意回到园外的小亭子中开始做爱,最后才回到她住的古堡的一间密室中继续做爱。
一个没有回忆的民族和国家,也不会有历史,如果没有回忆和历史,将来又代表着什么呢?照昆德拉的说法,就像书中开快车的年轻人一样,“他已经从时间的连续性中被抛开,他已在时间之外,他已进入狂喜之态,他已经忘了他的年纪、他的妻子、他的子女,所以他一无所惧,因为恐惧的来源是将来,所以一个从将来解脱出来的人无所畏惧”(见该书第2页)。对我而言,这个不会恐惧将来的人也没有将来。坐在昆德拉身边的他的妻子说:“法国每50分钟就有一个人在公路上撞车死亡。”这个人不是找死吗?
莫言:没有议论就没有昆德拉
我只看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为了告别的聚会》,很喜欢。跟拉美、美国作家不太一样,昆德拉生活在奉行极左体制的国家。他的小说是政治讽刺小说,充满了对极左体制的嘲讽。小说中的讽刺有一点儿像黑色幽默,又不完全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而且,这种对极左制度的嘲讽能引发中国人的“文革”记忆,人们很容易对那些描写心领神会,很值得一读。昆德拉的小说在结构上也很有特点,除了情节故事还穿插了大量议论,可以说没有议论就没有昆德拉。其中很多议论精辟、深刻,表现出昆德拉与众不同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