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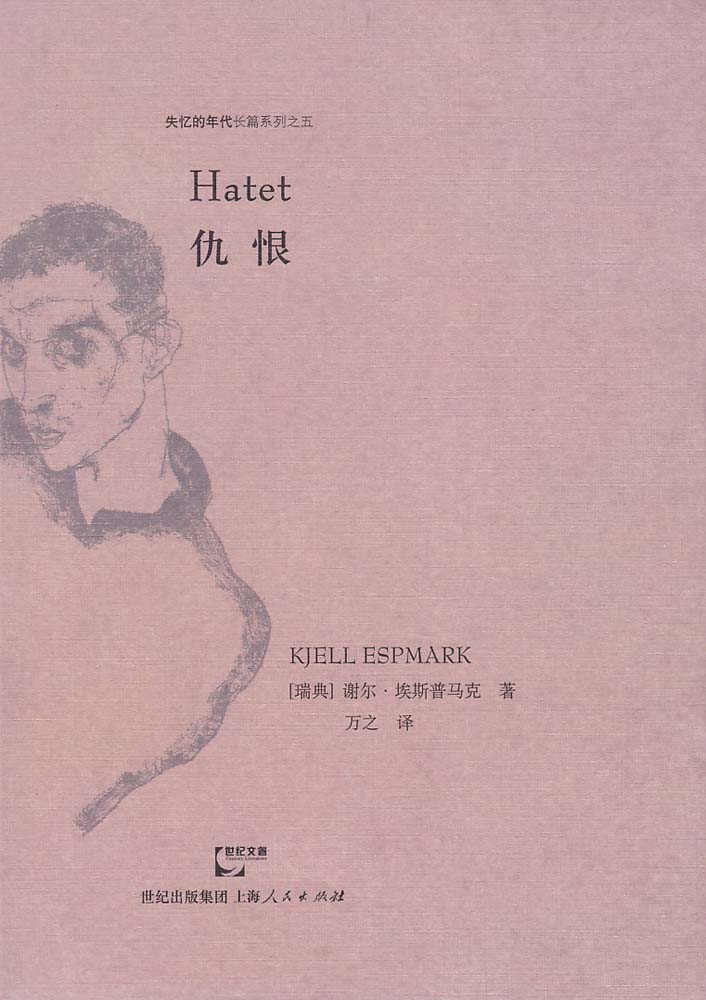 《仇恨》的主角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是出任过瑞典首相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乌拉夫?帕尔梅。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晚间,帕尔梅携夫人外出看电影,也没有任何警卫随行,电影散场后准备坐地铁回家,在地铁入口处遭刺客枪击,当场毙命。这个事件曾经震惊世界,因为瑞典当时被认为是世界最富裕最和平安宁的福利国家之一,发生这样残忍的刺杀国家领导人的事件令人难以置信。 《仇恨》的主角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是出任过瑞典首相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乌拉夫?帕尔梅。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晚间,帕尔梅携夫人外出看电影,也没有任何警卫随行,电影散场后准备坐地铁回家,在地铁入口处遭刺客枪击,当场毙命。这个事件曾经震惊世界,因为瑞典当时被认为是世界最富裕最和平安宁的福利国家之一,发生这样残忍的刺杀国家领导人的事件令人难以置信。
事件发生之后,瑞典政府曾成立专门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调查,并重金悬赏能帮助破案者,但事过二十八年,这个谋杀案依然没有破案,谁是真正的凶手依然还是一个未解的谜。案情扑朔迷离头绪繁乱,有的线索指向国际的背景,涉及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政权或者南美洲的新独裁者,也有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独立党到前苏联的克格勃秘密警察等等;有些线索则指向瑞典国内的极右翼分子,甚至事件发生的当晚警察和安全部门内部的电话通讯都非常可疑,更给人某种政治阴谋的味道。而某位主持调查的官员又曾言之凿凿地宣布,这次谋杀背后没有发现任何组织背景,纯粹只是某些仇恨帕尔梅的个人一时性起的丧心病狂的行为,个别嫌疑犯因此被捕,但最终都因为缺乏证据而释放。
《仇恨》作者从一个文学家的视角出发,以独白小说的形式,对这次事件的人物命运和内在逻辑做出自己的大胆解释:仇恨。失忆的年代中唯一还具有记忆的是仇恨。仇恨是人的本性之一,也是人性的弱点,是人自身构成的地狱。在作者的解释中,帕尔梅的强烈个性已经导致对他个人的强烈仇恨,是仇恨包围了他,最终也吞噬了他的生命。这种仇恨可以来自各个阶层,也可以来自各个方向,可以来自不同利益集团也可以来自不同信仰团体,可以来自政治右翼也可以来自自己的政党内部,可以来自国家政权也可以来自个人,可以来自国内也可以来自国外。作者甚至写到,由于帕尔梅的个性导致社会民主党民意调查支持率的大幅下降,连社会民主党内都有人要摆脱他,那么他的死甚至是符合本党利益需要的必然结果。难怪小说发表之后曾引发瑞典社会民主党对作者的强烈抗议,在瑞典社会也引起激烈反弹。对此,作者曾辩解说,文学虽然描述政治,但文学不是政治本身,文学家有自己的想象和表达的权力和自由,可以对生活做出自己的结论。
简言之,《仇恨》描述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帕尔梅毫无疑问是个理想主义者。正如小说的描写,他本来出身于瑞典名门望族,属于富有的上层阶级,却成了他那个阶级的反叛者,面对贫富的差距,他感到自身阶级的罪责和耻辱。小说开始写到他砸毁家里地下储藏室里的食品的行动,是这种反叛的开始。而他所爱的佃户女儿因贫病而死,也导致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和批判。一个挪威难民对他的教训,让他懂得个人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因此,他要致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而且没有贫富差距的理想社会,也就是一种起源于乌托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他因此放弃了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加入了工人阶级的队伍,甚至成了社会民主党领袖,为这个党通过议会道路连续执政立下过汗马功劳。帕尔梅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或者如小说中说的,是个“煽动家”,有一个政治家需要的卡利斯玛魅力,能动员群众跟着他走,所以曾两度赢得大选,出任瑞典首相(1969-1976和1982-1986)。此外,帕尔梅在国际上也非常活跃,敢于对抗超级大国的势力,既带头反对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又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帕尔梅总是站在弱小贫穷者一边,因此得到很多人的爱戴,但也招来很多人的忌恨。
了解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社会民主党其实是从共产党里分化出来的,其思想资源基本是相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在北欧势力一直非常强大。我到北欧留学并定居下来也近三十年了,而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都会在奥斯陆或者斯德哥尔摩的街头看到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游行队伍,而社会民主党或者共产党的领袖们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到处红旗招展,到处是镰刀斧头的符号,到处有人高唱国际歌。这种工人游行的场面在我的祖国都已经见不到了,没想到我会在这里重温旧梦。
当然,社会民主党不同于共产党,他们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而是走议会道路,通过民主选举的手段掌握政权。瑞典就是世界上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最早通过大选当政的国家。在经济上,社会民主党并不像共产党那样主张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完全国有化,而是通过税收来缩小贫富差距,达到社会公正。如果说,共产党是杀富济贫,那么社会民主党人是劫富济贫;如果说共产党人是要无产者要联合起来消灭有产者,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则主张无产者和有产者都要联合起来。所以帕尔梅有一句名言:“从来就没有他们,只有我们”,用中国旧式的表达方式,大概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