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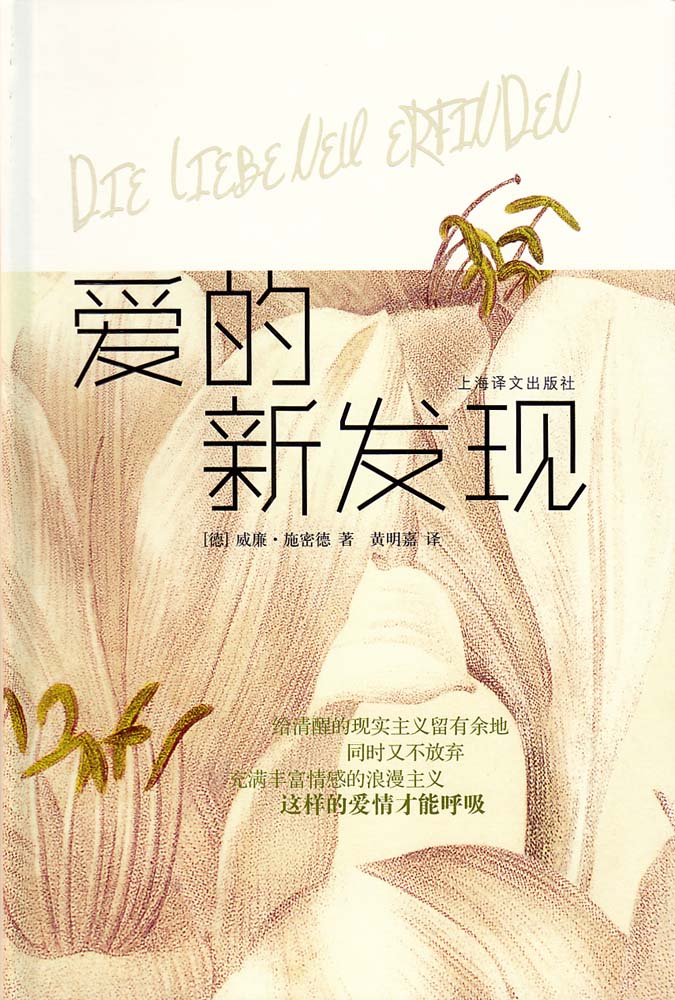 同他人交往,全都与爱和爱的缺失相关。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爱情的缺失,在许多人看来,这爱情无非就是男女“那种关系”罢了。这关系过去大概从未出现过问题,成问题的倒是另有原因。恰恰是人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爱情自由”在摆脱宗教的规范、传统的角色分配、习俗的观念以及摆脱为繁衍后代而相爱的自然目的之后,在现代社会里却出现了问题:自由的爱情显得十分棘手,越来越直白地提出“为什么”和“为何目的”这类问题。在某个历史时期,“浪漫主义爱情”向人们许诺无限的幸福感并以此回答了爱情的意义问题,直到它自身在所期许的美好情感与未估计到的麻烦之间被碾成齑粉。它越来越陷于它不愿思索的有限性矛盾中。相爱者在浪漫爱情中寻求的“我的融合”与“我的自由”诉求——不能忍受限制——相冲突,每逢失败,受质疑的便是比爱情本身还要多得多的东西,包括与生活和世界的关系。于是,浪漫爱情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突变成一个巨型水母,它用看不见的丝状物将柔弱的生命缠绕、分解并吞食之。有些人出于宗教热情仍相信它:另一些人则对它彻底失望;还有一些人怀着毕竟曾经有过爱的伤感而妥协,满足于以下认识:爱的情感是成分复杂的鸡尾酒,当醉意消散,此酒也荡然无存。 同他人交往,全都与爱和爱的缺失相关。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爱情的缺失,在许多人看来,这爱情无非就是男女“那种关系”罢了。这关系过去大概从未出现过问题,成问题的倒是另有原因。恰恰是人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爱情自由”在摆脱宗教的规范、传统的角色分配、习俗的观念以及摆脱为繁衍后代而相爱的自然目的之后,在现代社会里却出现了问题:自由的爱情显得十分棘手,越来越直白地提出“为什么”和“为何目的”这类问题。在某个历史时期,“浪漫主义爱情”向人们许诺无限的幸福感并以此回答了爱情的意义问题,直到它自身在所期许的美好情感与未估计到的麻烦之间被碾成齑粉。它越来越陷于它不愿思索的有限性矛盾中。相爱者在浪漫爱情中寻求的“我的融合”与“我的自由”诉求——不能忍受限制——相冲突,每逢失败,受质疑的便是比爱情本身还要多得多的东西,包括与生活和世界的关系。于是,浪漫爱情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突变成一个巨型水母,它用看不见的丝状物将柔弱的生命缠绕、分解并吞食之。有些人出于宗教热情仍相信它:另一些人则对它彻底失望;还有一些人怀着毕竟曾经有过爱的伤感而妥协,满足于以下认识:爱的情感是成分复杂的鸡尾酒,当醉意消散,此酒也荡然无存。
除了别的原则,哲学也许对解释和消除爱情中遇到的困难有所帮助。正巧,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爱,字面上的意思是“爱智慧”,以智慧为取向。人从哲学里获取灵感,更彻底的理解、更周密的思考、更审慎的行动,更自觉的放弃,凡此种种无不渴求智慧。推究哲理就是停下来作思考,研究已有的经历,从中得出结论,为未来的经历做准备。思考中,一再更新的生活取向是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的一个基本理念,也是自康德以来启蒙运动的一个明确的诉求。推究哲理者都致力于更透彻理解事物的关联,以便在生活里对种种关联妥善处置。思考的取向能使人清醒地过日子,享受“生活的艺术”。纵然没有哪种生活一直是完全清醒的,但必然有一种生活善于利用生活中的“醒豁时刻”。
此书针对爱情的思考,其目的是对急迫的问题找到可用的、但几乎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答案:爱情为何如此困难、但又为何仍然活力不减?对爱情说出结论性的话,这样做也许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但思考的取向可帮助个体更清醒地放弃它,或重新觅到它,或重新营造它。柏拉图《申辩篇》这部最早论爱情的哲学著作记录苏格拉底一度忙碌研究之事:“做爱情的强者”,此书也想尽力为阐发苏格拉底这一思想作贡献。在苏格拉底时代尚被接受、但到了现代社会则遭拒斥的同性恋也将一并述及。本书凡谈及“他人”处,这“他人”既代表男性,也代表女性。“他人”的单数绝不排除被爱者是复数的“他人”;“他人”是复数时,施爱者大多只是既定的单数“他人”。
哲学之路乃思索之路,“思索”字面上与寻求“意义”和产生“意义”相关。这种必要性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进入人们的视域:当事物各种关联消失,从出现的空位中可以感觉到生活缺少哪些关联。凡“制造意义”的东西就是关联,但它们在客观性和定义上并不是简单的固定存在,而要不断地予以思考和阐释。采用哲学的“阐释”方式,让人感兴趣的不是随心所欲的阐释,而是可信的阐释,所谓可信,是因为这阐释是可以领悟的,令人信服的。当某种现象的价值和重要性被领悟之时,名叫“意义”的特殊意义就显示出来了。此书与爱情相关的哲学思索针对以下问题:到底什么是爱情?它如何产生?如何发生作用?对生活有何意义?渴望爱情有何意义?爱情并非只代表爱情本身,它具有整体文化和社会范围的意义:那么,生活中其他种种人际关系与爱情何干?爱情嵌在何种关系中?它在某种文化和社会的思想天空里何处安家?它被分派何种角色?人们如何从爱情中看出生活意义?或当爱情失败时,如何让自己不至于因生活无意义而陷入绝望?当思考和阐释摆脱流行的观点时,人们也会探询还有哪些爱情观念,为实现爱情需做哪些必不可少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