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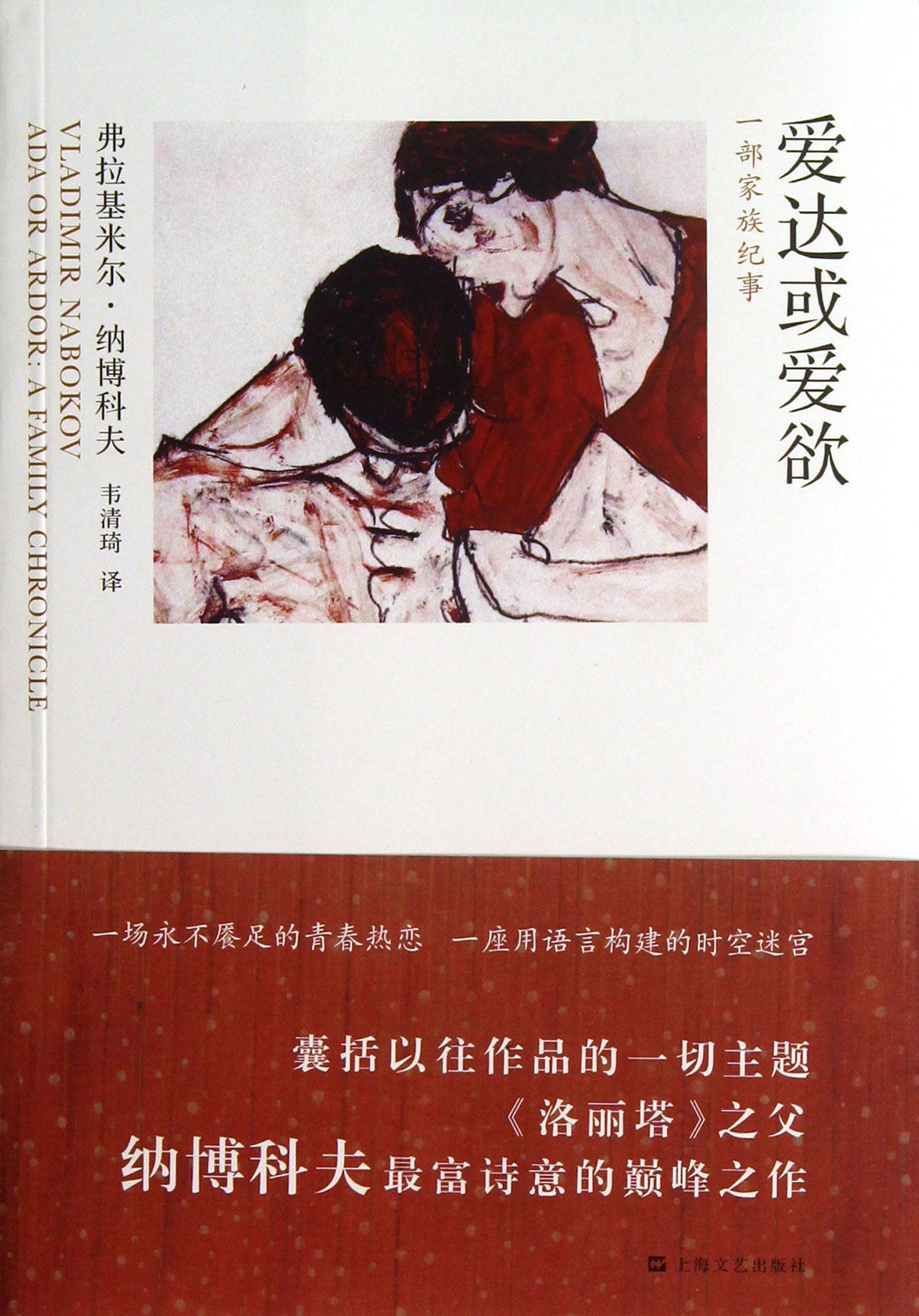 1969年,纳博科夫出版了其创作生涯中篇幅最大的作品《爱达或爱欲》(以下简称《爱达》),并且藉此书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一般而言,《时代》封面人物要么是成就极大,要么是争议极大的人物,纳博科夫可谓身兼这样的双重身份。论成就,他的《洛丽塔》、《微暗的火》足以傲视群雄,论争议,他对禁忌题材的兴趣,对道德的漠然,对文艺潮流的评骘,无不触动人们的神经。 1969年,纳博科夫出版了其创作生涯中篇幅最大的作品《爱达或爱欲》(以下简称《爱达》),并且藉此书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一般而言,《时代》封面人物要么是成就极大,要么是争议极大的人物,纳博科夫可谓身兼这样的双重身份。论成就,他的《洛丽塔》、《微暗的火》足以傲视群雄,论争议,他对禁忌题材的兴趣,对道德的漠然,对文艺潮流的评骘,无不触动人们的神经。
《爱达》聚集了所有争议的焦点:一个兄妹乱伦的不道德题材,却写得如诗画般美;作者创造了一个模拟地球的反地界,却从不与真正的现实相关。道德问题我们之后再谈,先说说“真正的现实”。纳博科夫因十月革命和希特勒上台逃离俄国和欧洲,最终流亡美国,他的人生经验不乏沉重敏感的话题,但他的作品从不探讨这些东西。同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昆德拉、桑塔格这些新文学感受力的倡导者一样,纳博科夫坚持认为,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是形式、风格,而不是社会、政治、历史的主题。《爱达》的反地界时空背景设定即是他对这类东西恶作剧般的嘲弄——美国军队在鞑靼人土地上遭遇一伙哈扎尔人的伏击——假使有人从中读出美苏争霸,或者更糟糕的,“年老的欧洲诱奸年幼的美国”或者“年幼的美国蛊惑年老的欧洲”之类的玩意出来,恐怕是要受到他无情的讪笑的。
纳博科夫对道德议题如同对时代、历史、社会的反映一样付之阙如,这归因于他的艺术观。在他看来,文学不是道德说教的演练场,如若用道德眼光看待艺术,那么,《安娜·卡列尼娜》只是通奸女人罪愆报应的宣传品,卡夫卡的《变形记》只是失去了赚钱能力的人被至亲鄙视至死的伦理剧。在纳博科夫的艺术场域中,文学有其自身追寻的目标,而道德从来不是其中的关键词。他无视舆论对其罔顾真善美的鞭挞,正如舆论无视艺术并非表达真善美的最佳载体。
但社会的力量是强大的。这就难怪包括博伊德在内的“挺纳派”,汲汲于在纳博科夫的文本中寻找可以为其辩护的道德符号。围绕《爱达》的道德争论,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凡是否对同母异父妹妹卢塞特的自杀负有道德义务。卢塞特是个跟踪狂,誓将自己的处女身献给凡,凡明确表示拒绝,卢塞特最后投海自尽。对此,博伊德评论说:“纳博科夫提请我们重新审视凡和爱达的恋爱与卢塞特之间的关系,他们追逐激情时对作为一个人的卢塞特的漠视”,继而,他从“纳博科夫很渐缓地让我们发掘凡的浪漫激情所包含的盲目性”,来推导出作者对这种激情抱持一种深刻而严厉的批判。但我们知道,爱情恰是漠视、盲目和排他的。那么,凡要怎样才能在不伤及卢塞特身心的状况下,将这个电灯泡推置一边呢?
凡意识到自己对卢塞特的欲念中有性无爱,并且与之牵手只会引起不下于与爱达更大的道德风波,因此他选择自渎而不愿与之同欢。对这样经审慎考量的想法,博伊德则全然回避而代之以一种审美分析:“他正是发觉了卢塞特的绝对真实性,与他经历的不计其数的女人的虚幻性形成的反差,促使他逃离真实。”凡就这样处于一种道德上的两难处境,他拒绝卢塞特是错误,接受她也是错误。那么,是否就该考虑这样一条出路:凡与卢塞特一夜情,然后让后者满怀感激地将初夜记忆连同可能暗怀的珠胎遁入精神病院,了此残生,同时,也皆大欢喜?其中的伪善我们暂且不论,按照博伊德的说法,既然卢塞特是“绝对真实性”的,那么,这种虚幻的结局不是从根本上击碎了绝对真实性的神话吗?
因而,纳博科夫在小说中对道德的不置可否,有其深意在。我们站在自身角度所作的阐释,可能狭隘化了作者和文本的观点,使道德问题沦为一个非黑即白的简单论调,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纳博科夫对由道德引发的一些更为重要的话题,比如“庸见”有着更为清晰的批判姿态。在《爱达》中,他把庸见定位于人们对乱伦的思维惯性上,“如果我描写乱伦意在代表一条可能通向幸福或不幸的道路,那我就是一个表现普遍观念的畅销书说教者了。”
显然,纳博科夫并不忙着给乱伦贴上合法或非法、道德或不道德的标签,而是对人们的庸见表示质疑。我们不必详举小说中提到的生物学例证,想想荷马史诗中兄妹结合的各种桥段,就知道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人们并不以近亲通婚为耻,直到优生意识、婚姻及财产制兴起,同姓不婚方始成为婚姻的圭臬。回到《爱达》的乌托邦语境中,当科学足以解决优生学上的问题,而凡和爱达又没有财产上的纠葛,那么,羁绊他们的又是什么呢?从凡的老爸德蒙苦口婆心奉劝凡放弃这段不伦之恋的话语中,我们可以一窥究竟:“你迫使我不得不用上最陈腐的词汇,比如‘家庭’、‘荣誉’、‘稳定’、‘法律’。好吧,在我放荡的生活中,我收买过无数个当官的,可是无论你和我都没办法收买整个文化,整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