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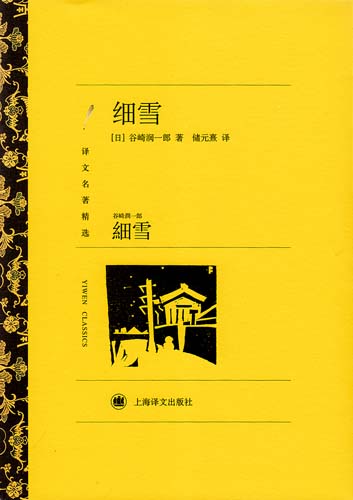 青年作家路内的文学启蒙,大多来自工厂里的图书馆。19岁就去工厂上班的他,“因为一天八小时就盯着几十个电表,也不用干活,只能看看文学期刊了”。 青年作家路内的文学启蒙,大多来自工厂里的图书馆。19岁就去工厂上班的他,“因为一天八小时就盯着几十个电表,也不用干活,只能看看文学期刊了”。
而在上班前,他就在爸爸的工厂图书馆里看书。路内现在还清楚地记得,1987年前后,他就是在爸爸的工厂图书馆里站着看完了半本《细雪》。
说起读《细雪》的缘由,路内坦承,其实是因为他当时的偶像主演了一部电影。“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有一部市川昆导演的《细雪》,是吉永小百合主演。我初中时特别粉她,上海电视台经常放这部电影,当时叫‘故事片’,电视报上有预告,下午放这部片子,我就逃课在家看。”
因为偶像演了电影版的《细雪》,“所以追溯到小说,也就很入迷了”。
去年底出版了最新长篇小说《花街往事》的路内说,《细雪》对他写作的影响还蛮大,“也许以后会写一个当代风俗小说吧”。他收藏了四个不同译本的《细雪》,可见爱之深切。
四个译本
在工厂图书馆里,路内看到的是1985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周逸之译本。如今这个版本已经绝版,“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八十年代都出版过一些很好的外国文学译本,后来版权正规了,这些译本也就废掉了”。
“后来周逸之的译本很难买到,市面上有的大多是上海译文的译本,储元熹翻译的。”储元熹的译本初版于1989年,从属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相较于周逸之的译本,储元熹的译本“应该说是更权威些”。后来,它也成了中国大陆最通用的译本,光上海译文出版社就不断再版,至少有四个版本,最近的一次再版是在2011年。路内当年就买过1989年的初版,“当时我二十多岁,有很多本‘二十世纪外国文艺丛书’里的书,其中就有这个译本。”如今非常珍贵,“在淘宝上卖得‘恶贵’”。可惜的是,这本书被人借走后再也没有还回来,“再后来,它卖到800块”。
“我再去买储译,就不是这个套系了,都是新版的,纸张和排版都一般,封面也都是和译文社那个普及丛书一套的,很难看。最‘刮三’的是,出版谷崎润一郎文集居然没有收《细雪》。”
对于这样的编辑思路,路内很郁闷。2006年时,他路过上海的一个旧书店,看到台湾版的《细雪》,“我问店主多少钱,他说30块。这是白菜价格,而且全新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卖这么便宜”。于是,毫不犹豫地拿下。
这是台湾远景出版社在1987年推出的魏廷朝译本,“恐怕在台湾都很少能看到了吧”。但是可能因为出版年份太早,印刷和纸张也都一般,于是路内又去旧书店买了周逸之的版本。2011年,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林水福的新译本,路内也赶紧买了。“但是800块的那个始终买不起,等我发财了再说吧。”
相对于大陆的两个译本,台湾地区的翻译“都还可以的”。“台译欧美文学有时候会隔一层,做日本文学那真是当行本色。”
“太正常”的日本小说
回到阅读《细雪》的最初。
路内在工厂图书馆里站着看完了半本小说,情绪却在这里有了转折。“那时候觉得小说不对啊,啰里啰嗦的。电影的那种视觉美感在小说中体现不出来。”
“小说中的女主竟然有脚气,脚气啊!”
被称为唯美派大师的谷崎润一郎,为什么会在小说中有这样的设置,路内当时也很纳闷。“小说写的那个时代,脚气大概是一种很普遍的病吧。”他只能这么解释。
路内说,相对于谷崎润一郎的其他作品,《细雪》也是个例外。“他的其他作品蛮异色的。”后来,他读到《疯癫老人日记》,“其实是另一种套路,里面说他年轻时睡过男优,好歹也算让我惊喜了一把”。
“谷崎润一郎是个有点怪异的人,这不奇怪,《细雪》却是个太正常的小说。所以,像贾平凹写得出《废都》,也是一个反向的例子吧”。
不过,谷崎润一郎在《细雪》中舒缓悠然的叙事风格,成为其特色,也成就了这部小说。这种缓慢的节奏,与人物的心理活动相重叠,营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他这本书就是拉拉杂杂讲风俗,定义为‘风俗小说’。我看了觉得故事节奏很慢,没有什么波澜,也不算难读,这个写法蛮影响我的。我十几岁的时候看小说没有这种判断,是个小说都能读下去,而且觉得日本人写小说么,就是这么慢吞吞的,很细致的,没什么故事的。”
这样的叙事风格影响了路内,他说或许以后也写一部当代风俗小说。“写风俗小说很难的,作者要人情练达,还要有一颗百科全书式的心。我想最重要的一条是,对于写拉杂的生活,如何用作者自己的心性去收拢这一堆破事,将其作为一个深具内涵的作品呈现(弥漫)开来——这样一种能力。也许《花街往事》会受到一点点启发。”
路内不停地感叹,现在的日本都没有谷崎润一郎这样的作家了,引进过来的都是杀人分尸之类的小说。“反正,日本文学是很可惜的。”而在他读《细雪》的那个年代,大家还不知道东野圭吾是谁。
最近,路内又将《细雪》的电影找了出来,重看了一遍。没有重读小说,他说:“我要选樱花开放的日子看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