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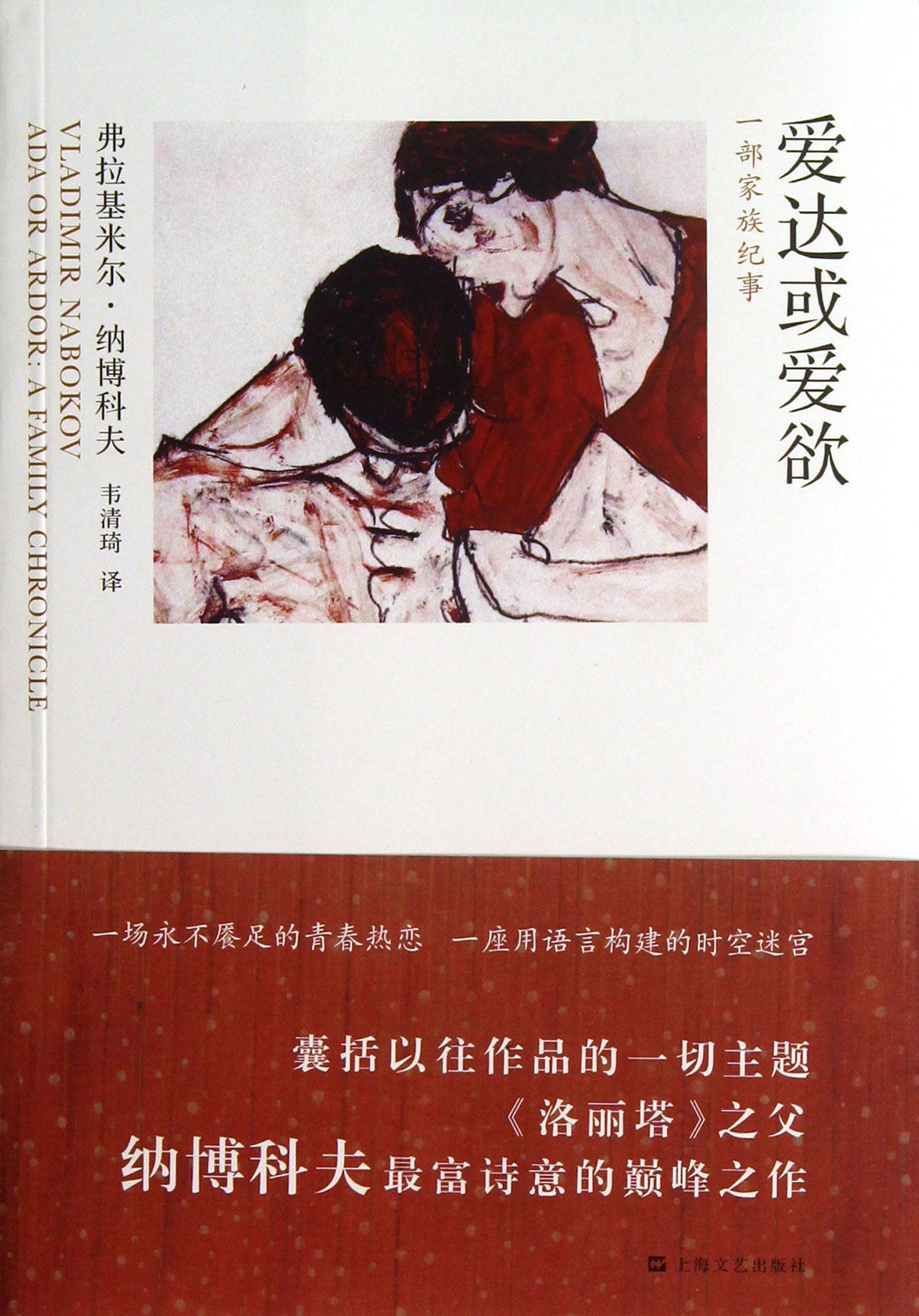 1968年9月,纳博科夫接受BBC采访时说:“我所有小说的功能之一是要证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是不存在的。我写的书是一个主观的、特殊的事件。我写作中根本没有什么目的,除了把书写出来。我写得很辛苦,长时间地遣词造句,直到我完全拥有这些词语并享受写作的快乐。如果读者的阅读也是一种劳作,那么读得越辛苦,效果就约好。艺术是困难的。容易的艺术是你在现代展览上看到的展品和涂鸦。”其时,纳博科夫正在创作《爱达或爱欲》的第四部《时间之肌理》,这是小说主人公凡,一个哲学家,早年的一篇研究时间本质的论文。他预计这个短小的部分会给他带来麻烦,但是写作异常的顺利,他用了三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本小说中最为艰涩的部分。 1968年9月,纳博科夫接受BBC采访时说:“我所有小说的功能之一是要证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是不存在的。我写的书是一个主观的、特殊的事件。我写作中根本没有什么目的,除了把书写出来。我写得很辛苦,长时间地遣词造句,直到我完全拥有这些词语并享受写作的快乐。如果读者的阅读也是一种劳作,那么读得越辛苦,效果就约好。艺术是困难的。容易的艺术是你在现代展览上看到的展品和涂鸦。”其时,纳博科夫正在创作《爱达或爱欲》的第四部《时间之肌理》,这是小说主人公凡,一个哲学家,早年的一篇研究时间本质的论文。他预计这个短小的部分会给他带来麻烦,但是写作异常的顺利,他用了三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本小说中最为艰涩的部分。
我们能够从纳博科夫接受采访中感受到他的那种高高的距离感,那种作家的傲慢,对读者和评论家古老的敌意。这位《洛丽塔》的作者,对任何曲解他作品的人,想从他的作品中窥探他八卦的人,对那些读不懂他作品还自以为是的人都充满了厌恶。所以他经常接受书面的采访,不想用对谈来浪费时间。也许更多的是,他想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写作上。正如我们现如今看到的,《爱达或爱欲》是他篇幅最长,最富野心的作品。经历过《洛丽塔》一系列的成功之后,他有了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创作一部真正宏大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不用考虑读者的感受,他只享受写作的愉悦——他心知肚明,他的任何一部新作都会引来很多出版商的追捧。小说还没有写完,好莱坞制片商已经陆续登门要求阅读手稿,每个人都要拿一份打印稿,并且在走之前将标书放在纳博科夫的地板上,“就像诸侯给皇帝进贡一样”。
但是无论是出版商还是好莱坞片商都低估了《爱达或爱欲》这本小说的难度。纳博科夫制造了一种高难度的写作,肆无忌惮地挥洒着自己的才华,在书中任何一个段落中都能找到他故意制造的语词陷阱,通过大量的双关语、互文式的联想、戏谑名著中的章节和人物、还有一贯地对记忆中细节着迷式的打磨,给读者阅读这本小说制造重重的障碍。在开篇的部分中,如果你缺乏足够的耐心,甚至都无梳理清这个家族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这是作者故意制造的阅读故障,仿佛提醒我们,如果你不是一个足够有耐心和有兴趣的读者,如果你无法欣赏作者的写作,最好不要涉猎本书的阅读。小说在纳博科夫的笔下已经不仅仅是讲故事的方式,而是一种诠释世界,表达自我意识的媒介。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布赖恩·博伊德所言,《爱达或爱欲》是纳博科夫对世界进行拆解、重组最为彻底的一次尝试:“他从声音与语词、色彩与轮廓、事物与任务、时间与事件那些仓促、复合的花样中建构了他的反地球,其网络之繁复是对我们这个地球的模仿,要厘清其意义却障碍重重。不过,意义始终在那里。”
在我的阅读印象里,纳博科夫之所以把小说背景搁置在一个反地球之上,制造了一种科幻小说的假象,主要是为了堵住世俗的偏见。经历过《洛丽塔》的系列风波,他已经厌倦了读者与批评家对他作品的任意而粗暴的解读。恋童癖与色情小说是贴在《洛丽塔》上面最多的词汇,在《爱达或爱欲》中,小说中的主人公凡与爱达从十二岁开始兄妹偷情,长达数十年之间的乱伦之恋,这种惊世骇俗的爱情小说场景比比皆是。纳博科夫赋予凡和爱达巨额的财富、高贵的出身、过人的智慧、强健的体魄、不知疲倦的性能力和炽热的私情,一直维持到九十岁的高龄——他们的长寿与爱情仿佛是对人世间虚伪道德的嘲讽——他们深深地陶醉在自己的爱情故事当中,他们在回忆中津津有味地互相提醒对方模糊的细节,重构了他们的少年之恋。如果按照世俗的标准衡量,我们基本可以想象出评论家面对这样一部作品时的言辞激烈程度。
小说在1969年5月出版后立刻吸引了大批读者关注,它上了《纽约时报书评》的头版,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成了《花花公子》厚厚的内页。《纽约时报》评价这部小说是“一部绝对原创的想象之作,再次表明了纳博科夫是跟卡夫卡、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比肩的作家……一部爱情故事,一部情色杰作,一次对时间本质的哲学探讨。”但是,纳博科夫的成功随后激起了同样激烈的反应。评论家菲利普·汤因比说,它是一部“有着顽强地裸露癖的骇人之作”;《伊甸园之门》的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发表了《纳博科夫的愚蠢》一文,说《爱达或爱欲》是十年来最被过度赞美的小说。很多作家都把这部作品比作了乔伊斯的的天书《芬尼根的守灵夜》。这点让纳博科夫很恼怒,他讨厌那部用奇怪的语言堆砌起来的天书,他拥有乔伊斯所缺乏的讲故事的天赋,能够利用这么多古怪的知识讲好一个爱情故事,而不是故弄玄虚。事实上也是如此,当我们撇开那些不堪卒读的部分,舍弃那些长篇大论的考据知识,深入到这个故事的核心部分,我们仍然能感受到纳博科夫对初恋的那种回忆的痴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