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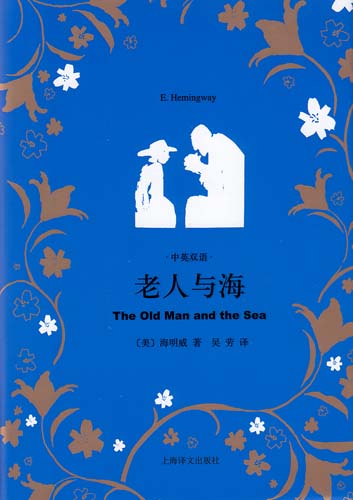 如今算算,至少得往回数七八年的光景。从那时起,吴劳见到我就会说:“小黄你写这个写那个怎么不写我呢?我真想看看你怎么写我啊。不过,我又想,如果你知道会让我看,就写得拘束了,就不敢说真话了。这样想想,还是等到我死之后,你再动笔吧。” 如今算算,至少得往回数七八年的光景。从那时起,吴劳见到我就会说:“小黄你写这个写那个怎么不写我呢?我真想看看你怎么写我啊。不过,我又想,如果你知道会让我看,就写得拘束了,就不敢说真话了。这样想想,还是等到我死之后,你再动笔吧。”
我总是回答得很干脆:“就你这么好的精神头,我哪有机会动笔啊?”
这话不是揶揄,更不是客气——我知道,吴劳平生最恨的就是“假客气”。跟他说话,我若加个“您”字他就要鄙夷,一口一个“吴老师”也会显得别扭生分。
“格宁,哪能哈西?”(人怎么能死呢?)吴劳总是操着一生未改的乡音(带着昆山腔的苏州话)质问我,然后不等我回答就一挥手将思路弹射到无远弗届。我起初还笑还争辩,小心地像对待其他老人那样避开所有不祥的字眼,后来我想明白了,不惮用“死”跟老爷子开玩笑,其实倒是等于跟他站在了一条战线上。“死”这种东西就在我们的谈笑间世俗化了,变得有形有迹有表情,仿佛可以拍着肩膀嘲笑,指着鼻子对骂——那不正是吴劳的强项吗?我以为,经过这些年的较量,他早就赢定了,或者说,早就跟它握手言欢了。
再往回数数,须得将吴劳的形象嵌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当年的情境里,我才能让画面在眼前活动起来。
每天上班,坐定,刚喝下半杯茶,就听到吴劳沿着木制楼梯拾级而上的脚步声。走一步,喘一步,叹一声,间或还夹杂几句自言自语。他一生音量惊人,哪怕在医院里卧床不起,一开口也能震得邻床的病友找护士投诉。可想而知,当年尚且硬朗时,他在楼梯上的“自言自语”,整栋楼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我想象不出,还有哪个单位,会有吴劳这样75岁的返聘员工,尽管晚来早走,但风雨无阻。“不给他发工资他也会来,”同事都这样说,“他离不开这里。”
在博闻强识(尤其西方文化)上,在查阅各种资料以解决翻译疑难的能力上,吴劳是当仁不让的权威,天晓得他浩瀚的大脑里分门别类地装下了多少索引卡片。
比方说,外文小说对话里随口提到一个人名,我们个个摸不着头脑,吴劳记忆里的某个抽屉却已经徐徐打开了。“是那个电影吧,格蕾丝·凯利演的,对,一定是。”说话间,他已经循着这线索,从一本厚厚的原版电影史后面的索引中找到了格蕾丝·凯利的词条,再从她的演艺生平里找到片名,最后从片名找到电影中这个人物的名字。“Bingo!”老头的脸上已经挂着掩饰不住的得意,就等我们尽情讴歌了。
都说吴劳过人的天分及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是社里的一座富矿,但你若想从中源源不断地挖掘出珍宝来,也不是一件没有门槛的事。你得具备横跨数十年的流行词语的基本储备,习惯他平均三句话里夹着五个字正腔圆的英文单词、外加一两句声情并茂的英文歌的特殊表达方式。
这些还只是皮毛,更要命的是,吴劳年逾古稀还成天接受各种庞杂信息,以至于思路跳跃到近乎奔逸的地步:上一句还在谈论寻常巷陌的水果摊,论述香蕉这种最适合老年人消受的水果是怎样一种尤物,下一句他已经在问你有没有听过麦当娜的《Like a Virgin》了。这时候不管听懂听不懂,你最明智的反应就是拼命点头。老爷子自己从早说到晚,也要求听众做出热烈的反应,否则你是要挨骂的。
每回去医院看他,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连说带唱,甚至说得更急促更时不我待,我连一个标点都插不进,只管听。是的,就像每每接到他的电话,一个多小时他也不会让你放下来,你只管听就好。太真实的人会映照得整个世界都为之尴尬,在我看,吴劳就是这样的人。如今,他在那边朗声嘲笑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谁还能听见呢?
(摘自东方早报 作者系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 此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