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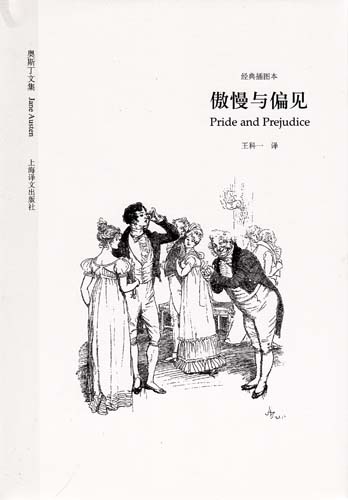 马修·刘易斯是18世纪末的英国作家,他的小说《僧人》仍然在版。他曾在信里跟自己的母亲说:听说她也在写小说,如果属实,千万不要出版,免得招来物议,自己丢脸不算,还会累及家庭。刘易斯生于1775年,与简·奥斯汀同岁。这说明,当时的风气并不赞赏女人写小说。奥斯汀的主要工作,据她侄子的推测,“是在共用的起居室完成的……她十分小心,不让仆人、客人或任何外人猜到她所从事的工作。”她在小碎纸片上写,或将吸墨纸放在一旁,便于随时遮掩。好在她的家人通达开放,对小说不仅宽容,甚至偏爱。《傲慢与偏见》于1813年1月问世,距今整200年。初稿成于1796年至1797年,用的是另一个题目——“初次印象”(First Impressions)。完稿后,老父亲为女儿联系出版商,但是人家看不上,只好拿回雪藏。小说从酝酿到面世耗时17年,其间的淡定忍耐,我们只能想象。 马修·刘易斯是18世纪末的英国作家,他的小说《僧人》仍然在版。他曾在信里跟自己的母亲说:听说她也在写小说,如果属实,千万不要出版,免得招来物议,自己丢脸不算,还会累及家庭。刘易斯生于1775年,与简·奥斯汀同岁。这说明,当时的风气并不赞赏女人写小说。奥斯汀的主要工作,据她侄子的推测,“是在共用的起居室完成的……她十分小心,不让仆人、客人或任何外人猜到她所从事的工作。”她在小碎纸片上写,或将吸墨纸放在一旁,便于随时遮掩。好在她的家人通达开放,对小说不仅宽容,甚至偏爱。《傲慢与偏见》于1813年1月问世,距今整200年。初稿成于1796年至1797年,用的是另一个题目——“初次印象”(First Impressions)。完稿后,老父亲为女儿联系出版商,但是人家看不上,只好拿回雪藏。小说从酝酿到面世耗时17年,其间的淡定忍耐,我们只能想象。
这本小说在奥斯汀的所有作品中并非最成熟的一部,却最受读者的喜爱,先后译成30多种语言,经常雄踞各类好书排行榜的榜首。《傲慢与偏见》发表后,颇受欢迎,当年即出第二版,4年后发行第三版。这在小说算不上优雅读物、出版业远没有今天热闹的年代,已属难得的景况。不过,那会儿的奥斯汀还称不上畅销书作家,司各特同时期发表的《罗伯·罗依》两周内就销了1万册,而《傲慢与偏见》的第一版只印了1500册。
故事的开场是班奈特夫妇的一番对话。第一章搭好了全书的框架:牧师班奈特先生有5个女儿等着出嫁,邻近的豪华庄园出租给阔少爷宾利,他还带来一位更富有的绅士达西先生。接下来的15个月,从头年秋天到次年的圣诞节,班奈特家的大女儿简和二女儿伊丽莎白吸引了宾利和达西,像很多爱情小说那样,两对有情人颇费了几番周折,才拨云见日,修成良缘。伊丽莎白和达西的恋爱是主线,简和宾利起衬托的作用。后面这一对性情相投,一如既往的好脾气,也缺少主见,故而他们的生活起不了大波澜,除非有外人作梗。伊丽莎白和达西不同。这两人一出场就有了麻烦,并且麻烦不是源于,或者说,不主要源于外因,而是来自他们自身的缺憾:一个过于傲慢,出言不逊,得罪了对方;另一个一味依凭第一印象,让偏见遮蔽了理智。一方需转变态度,另一方要消除偏见。奥斯汀讲的是恋爱故事,内里其实涉及自我认识、理想婚姻、美德与幸福的关系。小世界里有大关怀。
“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傲慢与偏见》的开场设计得很考究,一句话便交代了小说的两个关键词——金钱和婚姻,而且定下了反讽的基调。“举世公认”是一个反讽。据剑桥本的注释,这是奥斯汀对当时布道辞动辄用“举世公理”的戏仿,是否属实,我们不去穷究,但在小说里,“举世”并非真的“举世”,因为连班奈特夫妇俩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都南辕北辙。况且,真正着急的不是有钱的单身汉,反而是待字闺中的小姐,尤其是有5个女儿等着出嫁的班奈特太太。“举世”其实范围小得很,局限于浪伯恩村那些定要把自己的刻板法则或狭隘观念当成真理的人。
话说回来,嫁女儿确实是一桩大事,相比于班奈特先生的无动于衷,班奈特太太火急火燎的势利心态,虽是她智力贫乏的表现,却反映了当时女性生存的现实困境。19世纪的英国依然实行长子继承制。不属于长房家庭的中等阶级的男孩子,可以在商界打拼,在政界历练,也可以在法律、医药、教会等行业试试身手,总之,不缺乏谋生的手段。女子呢,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家庭作坊的衰落和集中化生产的盛行,反而渐次退出纺纱、织布、炼乳、农业和手工业等行业。所以,对于这一阶层的女子,几乎没有事业一说。如果有,也只限于贤妻良母的角色。依照常理,她们如果幸运,找个好人家嫁了,就算有了事业;倘若嫁不出去,只好寄人篱下,由父兄供养,像奥斯汀姐妹那样;境遇再差一些的,既无财无貌,又无所依附,就只能去当一名教师或陪护,勉强维持生计,像比奥斯汀晚一辈的勃朗特姐妹那样。与勃朗特姐妹同时代的哈丽雅特·亨特曾说:“女教师的工作得不到应有的评价,也得不到应有的报酬,价值几乎为零,自尊几乎丧尽,辛苦毫无回报,生活令人厌倦——自己呢,与下等人没什么差别——要受人挤压、贬低、蔑视、谴责,既疲惫不堪,又痛苦不堪。”如此困境下,她们倘若去“找一个傻瓜嫁了,从每天要过的令人心碎的生活中抽身出来,谁能指责她呢?”可见,婚姻对于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女子而言,实在是一个太自然的诱惑——它不仅可能满足情感的需要,而且是生存的“正道”,是社会承认的女子实现价值(为人妻母)的惟一途径。正因为如此,奥斯汀在写给侄女的信里说:“陷入贫穷,是独身女子面临的很可怕的一种可能性——这是人们赞成婚姻最有力的理由。”然而,现实环境再不利,结婚的理由再充分,该不该就找个傻瓜嫁了?《傲慢与偏见》对此显然有不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