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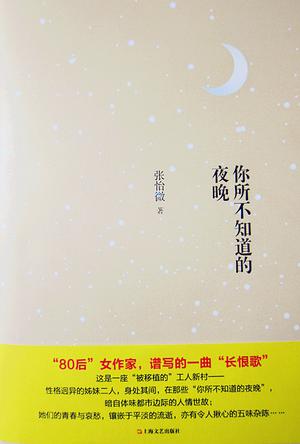 《夜晚》的构思来自于我童年以来所听到的、见过的种种新村人的模样。还原他们,就仿佛是重新认识自己的父母一辈,重新探索自己的来历、前史。我觉得这很有趣,仿佛充满了可能,怎么写也写不完。同时,又充满规则。 《夜晚》的构思来自于我童年以来所听到的、见过的种种新村人的模样。还原他们,就仿佛是重新认识自己的父母一辈,重新探索自己的来历、前史。我觉得这很有趣,仿佛充满了可能,怎么写也写不完。同时,又充满规则。
《夜晚》的故事很不新鲜,说的是上海,又仿佛是上海的背面——一个眼看着“上海”生活的小圈子。有平淡的流逝,也有流逝中的五味杂陈。在整理一些素材的时候,我觉得我仿佛看得到一种冲破时间的力量。那是人与人之间朴质的传承,与这个世界的变迁无关。是人的自识、人与人的相处、误解与原谅。
但这个故事,我还没有写完。
这种感觉就仿佛觉得“日子好像是过不完的”,遥遥无期,明天是今天的延续。但事实上,总有一种力量打破惯性的脚步,令平静的生活戛然而止。小说写到末尾,或有着这样的紧张感。仿佛突然被切掉一块,呈现出连着血肉的横截面。这个横截面,其实是我非常有兴趣的,即生活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变得那么苦涩、那么挣扎,变得那么需要勇气、需要狠狠心才能努力过下去。所有的平淡,都指向最后的不平淡。
从写小说的速度来讲,我是快手。但这个长篇,我琢磨了一年多,写写改改,仿佛一个实验、一个素描,非常朴质。我自己很喜欢的部分,是青青的离开,墙上的那把琴;以及杉杉与茉莉互相嘲笑“脖子歪掉”。写的时候就有失落,也有欢喜,仿佛又回到童年甜蜜的迷雾中。
这些年的写作使我渐渐发现,将对于生活的新认知、新观念内化成小说的故事,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仿佛观念越新,故事就越难表达。脱离观念,反倒是能将许多事情说圆。我没有飞扬叙事的能力,已经做的那一些,也不过裁出生活的留白,填补未尽的遗憾。
我的写法,似要消耗太多人情世故,而我的年纪,恐怕又实难消化厚重的生活容量。叙述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学习如何去爱父母,爱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因果。学会承受、体谅、欣赏那些没有是非的生存难题。这也是写作本身给予我的宝贵财富。
感谢父母。
二○一一年十二月,于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