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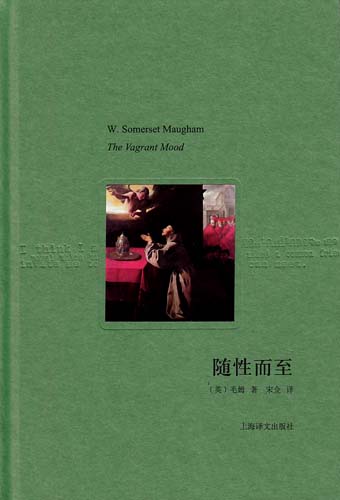 这本《随性而至》是毛姆备受推崇的一本随笔集。在这版的封底,编辑总结道:它风格多样,精彩迭出。这看似简单的八字却是我在读完全书后方才深深领会的。它带给人的感觉太过多面,就如一杯香茗,初尝觉得无奇,细品却口感丰富,回味则更是悠长。 这本《随性而至》是毛姆备受推崇的一本随笔集。在这版的封底,编辑总结道:它风格多样,精彩迭出。这看似简单的八字却是我在读完全书后方才深深领会的。它带给人的感觉太过多面,就如一杯香茗,初尝觉得无奇,细品却口感丰富,回味则更是悠长。
书中的六篇长文打通了记人随笔和文艺批评两个不同的领域,涵盖了最能体现毛姆本色的主题:人性、作家生活、美术、写作和阅读,所以他写来得心应手——叙事风格已临朴素之境,文字则炉火纯青。而毛姆本人善讲故事的才能更是在其中体现地淋漓尽致。
而尽管六篇长文所涉主题各有不同,但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当属对于人物的刻画——从哲学大师康德到硬汉侦探小说家钱德勒,从西班牙巴洛克画家苏巴朗到政治家伯克,从回忆录作家奥古斯都·海尔到“纯文学”作家亨利·詹姆斯……毛姆或通过撰写他们的生平传记,或通过品鉴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的造诣,或通过与他们进行美学论争,让这些人物的形象鲜活生动地跃然纸上。正如有评论说:“毛姆以其塑造小说人物的洞察力和讲述故事的高超技巧,既生动有趣又入木三分地活画出这些著名人物的性格、气质、怪癖乃至于灵魂”。
而与大多作家描写人物的风格不同的是,毛姆毫不讳言笔下人物的弱点,甚至到了刻薄的地步。他觉得伯克是“鲁莽的赌徒、无耻的揩油者、缺德的钻营之徒”,亨利·詹姆斯则太过古板,而作家威尔斯“性欲旺盛”,“从来没有真正爱过”,却又“确实令女人发狂”……但却正是因为被“揭发”至此,这些大人物们才显得真正立体丰满,与所有的凡夫俗子一样有着无奈的局限和窘迫。于是,在毛姆的描述之下,我们知道了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也知道了那些不光彩却实则人性使然的部分——他们之于我们,就像是老友。
毛姆自己也曾经说过:“我的个性决定了我不愿不假思索地接受一个人的表象价值,而且我很少被折服。我没有崇敬别人的能力。我的性格更容易被逗乐,而非敬重别人。”
对于描写人物的文学作品,我们关注的往往是被描绘对象是否能被刻画的入木三分、生动传神,但其实这只是露出水面的那部分冰山。王国维曾说:“以我观物,则物皆着我之色。”每个人都是多极多面的,哪一极哪一面被展现,全看作者如何选择,所以刻画人物其实最能显“作者之色”。
毛姆常常喜欢引用布丰的格言“风格即人”——意即风格是作家的创作个性,会在作品中自然流露。所以他常常喜欢通过他人的文艺作品来探究人性。他自承,他更关注的是人,而文艺作品是附带的。但同样,毛姆的作品也深刻地体现出他本人的特点。他和他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复杂难测的多面体。在这本《随性而至》中,毛姆笔下的人物无论怎样的大名鼎鼎,却大都是美德与缺陷的混合体,“在他们身上集合了相互之间如此抵触的优点和缺陷。”而毛姆行文风格的生动、犀利、嘲讽、冷静,都体现出他一贯以来的诉诸于个人的感受和分析的创作特点,更体现出他处世上平视前方,心态平和,不盲从权威的特质。“他喜欢站在远处静静观察形形色色的人物,不喜欢和人们面对面地交流,他内向、羞涩、拙于情感交流,但同时又理智、从容、对人性有着深入骨髓的洞察。人性是他站在画架前冷静描绘的客体,而非抒情的对象”。
常常看到有评论说,处于20世纪的毛姆,在行文风格上没有什么现代主义思潮的印记,在文学观念上已经落伍。而他也自称只是个较好的二流作家而已。但读完这本《随性而至》,我却觉得,对于人性的关注正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大特质,毛姆只是用了属于他自己的方式表述出来。一时之性情,万古之性情,毛姆对“人”的具有现代意义命题的关注,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传统与现代兼收并蓄的特征。
所以,毛姆从来不是一个时期、一个时代或某一个十年的发言人。他的作品不具有那种意义上的时代性,却具有着超越时代的内蕴和洞察力。从这点上而言,正如这本书名,毛姆真正做到了“随性而至”、不为时代潮流左右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