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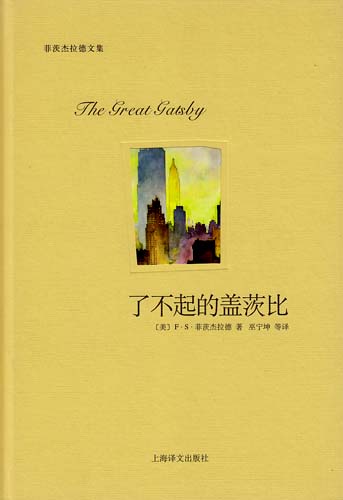 《1Q84》的日文版刚出不久,我就买来读了,然后在《书城》杂志上写过一篇算得上牙尖嘴利的评论。试引用部分如下:“剥开小说的外壳,作为读者,我发现村上的故事内核一如既往。从1985年到2009年,其实并无新的变化……这样的‘物语’,是否真能成为人心在脆弱中的依凭呢?” 《1Q84》的日文版刚出不久,我就买来读了,然后在《书城》杂志上写过一篇算得上牙尖嘴利的评论。试引用部分如下:“剥开小说的外壳,作为读者,我发现村上的故事内核一如既往。从1985年到2009年,其实并无新的变化……这样的‘物语’,是否真能成为人心在脆弱中的依凭呢?”
无爱便无恨。用这句话来形容我对村上春树小说的情感,大概恰当。正因为我在整个青春时代耽读他的作品,才会对其新作有大的期许和失落。毕竟村上的小说曾给我的生活带来隐秘和显著的影响,前者如冰层下的暗涌,后者则使我走上今天日文译者的职业道路。这影响不算小。
如果把时间翻回15年前,1997年,村上在中国的大热尚未到来。我初读《寻羊冒险记》就是在这一年。从福州路书店买来的这本书是漓江出版社的选集之一,黄色封皮上有幅抽象画,版权页写有印数,五千册。
村上后来的小说也常有失踪和寻找的伏线。失踪者往往是妻子、女友或母亲,仿佛是主人公“我”失却而不可得的理想。《寻》有些不同,找的不是人而是羊,故事中偶尔闪现的失踪者是男性,“我”的好友鼠。那是个写小说的浪游富家子,也是抛弃社会的遁世者。故事以主人公被迫找羊开始,以“我”和鼠的对谈结束,说是冒险,更像是荒诞日常的拼凑。随着故事层层展开,各色人等翩然出场:政治家的秘书,和上帝对话的司机,名叫沙丁鱼的猫,拥有无与伦比的耳朵的女友。故事性和幽默的对话使整本书有种从容的节奏,但这不是当时的我反复阅读它的理由。我的确读了很多遍这本书,在工作的间隙,在老弄堂旧居的床上,在一家深夜营业的酒吧。那家店的灯光明亮如快餐店,菜单上有种分量实在的三明治套餐,名叫“海陆空”,我有时在夜班回家的路上允许自己小小奢侈,坐下来点一份海陆空三明治伴读。以至于后来每次重读这本书,我总恍惚闻见薯条的气味。
到底是什么紧紧地抓住作为读者的我,让我反复进入一个故事,在相同的拐角徘徊、沉思,或蹙眉或微笑呢?
村上在后来红遍南北,赞扬和恶评同时肆意滋长。“小资教父”的称号未必是一顶桂冠。有评论家说,他文中的主人公总是那么孤独和自我,因此打动了当下年轻人的心。我从不否认自己是村上迷之一,但心里有那么一点儿不协调的劲头—我最初邂逅他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名字。那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我读的第一本村上。学校图书馆的书掉了封皮和前十页,用牛皮纸重新装订过,只剩下管理员手写的书名,连作者名也阙如。就这么一本残书,让我忍不住四处打探写书的人究竟是谁,并开始追寻他的其他小说。由故事到作者,再到故事。对特定作者的广泛和深入阅读肯定有气味相投的因素。读书是一种非线性的旅行,也是非血缘的“认亲”过程。有时候,作家在书中谈论他本人的阅读谱系,读者见了欣喜,一个个认过去,果然都有些似曾相识。
由村上到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就是这种走亲访友式的阅读扩散,他和我近年来喜爱的约翰·欧文都是村上翻译过的作家。初读《了不起的盖茨比》,差不多也是在1997年。乍看之下,两名作家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村上的小说多有魔幻和突兀的情节,菲茨杰拉德无疑是现实的演绎者。《寻》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与《了》的长岛和曼哈顿图景相差了近50年,盖茨比的梦想是那么生气勃勃,仿佛能席卷一切,而村上笔下的人物却多的是对现实的逆来顺受,顶多冒出几句反讽。但也许因为我把这两个故事都读过太多遍,以至于它们形成奇异的螺旋,如DNA般缠绕不休。
当时的我太年轻,阅读量也有限,以至于意识不到村上的每本小说都是之前作品的赋格式变奏,或者说“老调重弹”。无论作家是否有局限性,他带来的影响是真实的。我开始写科幻小说是在1996年,那会儿已开始读村上。我的第一篇小说带着孩子气的梦幻,写一个因事故残疾的女孩把自己的意识注入樱树,选择作为一棵树活下去。故事是原创的,写法却难免沾了村上的文风,或者说,干脆就是“林少华版村上”的语调。我花了差不多5年才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又费了很大的功夫自我矫正。说到“写作腔调”,不免提及人文社出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由汤伟翻译的卡佛,按理说和林少华翻译的村上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偏偏让我读出一百个相似。只能说,村上受卡佛的影响实在不浅,可能他本人都没意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