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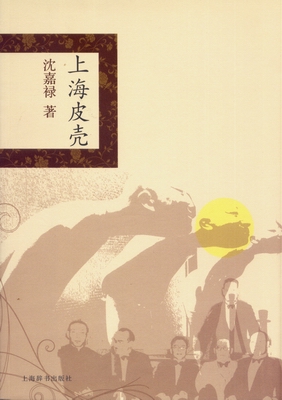 《上海皮壳》(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是作家沈嘉禄最新出版的文化随笔集,对于书名,作者在自序中这样解释:“这本书里所谓的皮壳,并非特指物理层面的表象,而是一个专有名词。如果你是一位古董爱好者,必将会心一笑:啊,老皮壳!”书中的文章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了上海城市历史与文化现象,并将着眼点放在城市与人的关系上,由此发现了一些文化研究上的空白,同时也对上海城市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进行了善意的批评,给出了不少建设性的建议,很值得一读。 《上海皮壳》(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是作家沈嘉禄最新出版的文化随笔集,对于书名,作者在自序中这样解释:“这本书里所谓的皮壳,并非特指物理层面的表象,而是一个专有名词。如果你是一位古董爱好者,必将会心一笑:啊,老皮壳!”书中的文章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了上海城市历史与文化现象,并将着眼点放在城市与人的关系上,由此发现了一些文化研究上的空白,同时也对上海城市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进行了善意的批评,给出了不少建设性的建议,很值得一读。
怀旧,对返乡无法实现的哀叹
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人似乎特别喜欢怀旧,我发现至少有几个原因:
社会发展太快,转型太过迅猛,人到中年的上海人(往往是社会主流群体)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被卷入一个陌生的新时期、新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人失去了许多东西,比如固有的彼此依存的人际关系、宽松的社会环境、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与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习惯等,这些东西像烟云一样散去,抓也抓不住,只能通过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来安慰自己。
比如在三十年前的石库门弄堂里,人与人的距离是很近的,几乎不设防。张家伯伯订阅的解放日报,李家阿叔是可以拿来先看的。钱家阿婆出去打麻将,不用担心下雨,晾晒在天井里的衣服,李家嫂嫂是会帮她收起来的。刘家小妹正在编结的羊毛衫,那种新流行的花色大家看着漂亮,她就马上教会大家。张家姆妈包的荠菜肉馄饨,煮好后会一碗碗地送给大家尝新。而现在,这种生态很难再现了。
社会矛盾的纠结,也使中老年朋友发觉自己坚守了大半辈子的价值观已经被热情拥抱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年轻一代所抛弃,自己的行止突然变得不合时宜,落伍了,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所以在精神上倍感失落,倍感孤独,倍感惶恐。诚如出生于苏联的美国作家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所言:“现代的乡愁是对神话中的返乡无法实现的哀叹,对于有明确边界和价值的魅惑世界消逝的哀叹;这也可能就是对于一种精神渴望的世俗的表达,对某种绝对物的怀旧,怀恋一个既是躯体的又是精神的家园,怀恋在进入历史之前的时间和空间的伊甸园式的统一。”
怀旧,再一次身份确定
再有一个原因,上海本来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城市的最大特点应该是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可以一切从零开始。移民从整体上说都是怀着一颗改变自己命运、获得社会承认的野心而来。但是在建国后的半个世纪里,因为户籍制度等原因,上海成了一个严防死守的城市,在各方面极其傲慢地排斥、抵制外省人,久而久之也造成了上海人的优越感和排外心理。
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的堤坝终于溃决,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可阻挡的城市化进程,成千上万的外来人口冲进上海,冲散了上海的居民结构。坚守了几代人的礼仪规则受到了嘲笑与颠覆,经几代人努力而养成的生活作派、契约精神被粗暴扭转。不错,查查上海人的根底,大多是移民而来的,但一旦成为上海人后,就很看重这个身份。而现在,上海的中老年朋友为了确认自己上海人的身份,就需要通过怀旧来证明自己曾经辉煌过,曾经见识过大世面的。
在另一层更自我、更内向的心理层面上,有不少人会认为自己本来很有潜质,也可以大有作为,但因为生不逢时,被时代的龙卷风高高提起,又重重抛到边缘地带,由此改变了人生的路径与走向。于是,歧路在伸展,差距在扩大,人的欲望也越来越大,如潮如汐的心绪难以抚平。今天,同样的年龄层,别人为何比自己更富有、更轻松、更潇洒?是因为他们更善于利用政策和机遇,或者更有胆量而已,并非自己“技不如人”,而是“时运不济”。不甘承认自己的落后现状,也需要通过怀旧来证明自己有一种可能被埋没的价值。
怀旧,成为一种时尚的消费形态
怀旧风尚的兴起,或许缘于上海学的兴起。学术研究对上海人怀旧的引导与暗示作用确实是很大的,何况还有媒体的推波助澜呢!不过海派文化在今天“凤凰涅槃”,在老百姓的层面则多半表现为具体的消费方式——包括精神与物质。上海人通过对历史的回望,重新发现或梳理了曾经的辉煌,因为这份记忆是足以傲视外省人的。所以这种对往事的回想,无意中就累积成了群体的财富,是一种值得显耀一番的资本,也有身份认同的意思在里面。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怀旧与时尚被调成三色鸡尾酒,插了一片文化的柠檬,由彬彬有礼的侍者端到大众面前。比如在有些上海人的家里,也会流于俗套,比如做一只假的壁炉,挂几张老照片,月份牌、年画、香烟广告等旧上海的符号也不顾一切地进入生活空间。有些人以为老上海一切都是好的。这其实是一种间接的经验,并不是亲身的情感记录。他者的生活,不能代表本人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