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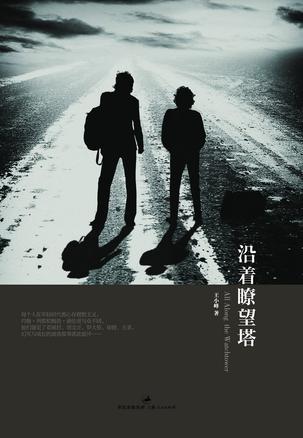 去伪存真的思想火花 去伪存真的思想火花
2010年留在记忆中的社科文史类好书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关于“中国速度”、“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讨论逐渐增多。毫无疑问,中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大发展大变革之中。在阅读时厘清思路,认清“中国崛起”、“中国责任”的本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基于此,今年社科文史类读物的出版在承袭这股思想热潮的基础上,佳作不断。
大多数的言论烘托少数的清醒
伴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中国模式”这个词逐渐在国外媒体中升温。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让这个概念变得炙手可热。而当这个承载着西方人复杂态度的概念撞上国人的眼球和心坎,激起的是更加复杂难言的波澜。
但热闹是一回事,对问题的澄清是另一回事。如同一切的喧嚣,大多数的言论烘托出的只是少数人的清醒和明智。按照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先生的话来说,西方的“捧杀派”或“崩溃论”者,同样是各怀偏见。
在郑永年先生看来,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中国近60年的发展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能否认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之处,但“中国模式”的确存在困局。重要的不是定性,而是从学理上深入、理性地来思考这个模式是如何而来,它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又陷入了何种困局,如何才能改进它,使它朝好的方向发展。
《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有助于我们超越“左”、“右”的门户之见以及那种对政治问题视而不见、回避不谈的鸵鸟主义,真正客观而清晰的理解中国政治、政局、政策。看完这本书,会让读者感觉到,中国政治的各领域、各类问题,都有自身复杂的历史积淀、利益纠葛,根本无法套用任何一种西化的政治框架和模式原型。
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国际学者,郑永年在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在国际上也颇有影响力。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郑永年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态度上的理性及务实,毫无某些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的偏激和狂傲,郑永年在对中国问题尤其是国内问题的建言上也极其中肯,基本上立足于中国国内的现实情况提出建议,而不像某些专家学者那样把西方那些东西拿过来生搬硬套,最后弄出来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对中国实际上有百害而无一益。
作为此书的着重点,郑永年花了大量的篇幅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生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尤其是在政治改革的民主化改革方面郑永年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
挑战一种话语霸权
《如何研究中国》是当代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曹锦清先生的又一部大书,是继《黄河边的中国》之后,曹先生继续密切关注当下大问题的一部力作,是一个学者对当下国情的新的观察与思索。在“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和社会科学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因此,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范式、理论视野及实证研究的范例都不可避免基于西方“现代化”的经验。与之同时,非西方的社会实践和学术资源基本都被遮蔽了。然而,正如后结构主义和新葛兰西主义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话语霸权从未也无法避免挑战。回复本土经验和学术反思乃至政治实践之间有机联系的努力正贯穿了现代社会科学范式扩展的本身。
曹锦清教授的努力或许提供了另一种学术路径。在这个学术路径中,中国不单纯是理论研究的对象,中国经验也不再是西方理论中的“他者”,相反,理论研究服务于认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不过于强调理论研究的“规范”,强烈的经世致用情怀成为曹先生学术之路的主要立场。在这本《如何研究中国》中,曹先生多次提到,他本人是因为对人生、对理解中国有困惑才有所作为的。早年《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启动时,是为了全面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到《黄河边上的中国》,则更加鲜明地表达了其对中国“千年之巨变”的关怀,如果说这些研究更多是曹先生早年“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的具体努力的话,那么,《如何研究中国》则更多的是对这些具体研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思考。
正如曹先生所言,在学科分化越来越精细,而中国社会却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认识中国”变得越来越困难。曹先生所言的“返回历史”,以及这个集子里多次提到的孔孟、朱熹、王阳明、孙中山、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等一大串名字,或许表明士大夫情怀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