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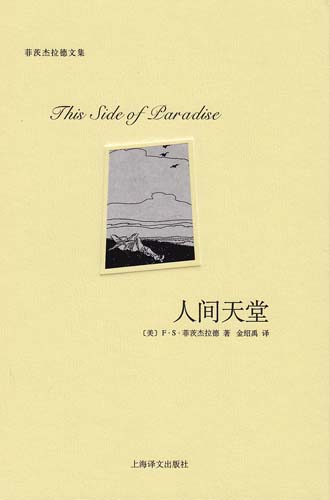 一 一
美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出生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城一个信仰爱尔兰天主教的家庭。一八九八年,全家搬到纽约州的边远地区,但在作家十一岁生日前,他们又回到他的出生地,所以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中西部人。不过,后来他被送往东部,在新泽西州一所贵族预备学校读书,毕业后就进了普林斯顿大学。在大学期间,他活跃在业余社交、体育和文学等活动中,但他的学业并不顺利(社交活动忙碌显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中途辍学,后又回到学校,终于在一九一七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军而永久离开学校。在军队的训练营里,他写下了第一部小说最早的初稿。
菲茨杰拉德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于一九二〇年九月出版,这部书的出版也并非一帆风顺,这里要提一提编辑、出版家麦克斯威尔·帕金斯(Maxwell Perkins,1884—1947)。帕金斯原是《纽约时报》记者,一九一〇年加盟著名的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Charles Scribner's Sons),编辑出版过约翰·高尔斯华绥、亨利·詹姆斯等大作家的作品,但同时他也有心扶掖年轻作家(菲茨杰拉德二十三岁,他第一次文学上的练笔则是十二岁时发表在一份校刊上的侦探故事)。菲茨杰拉德的第一部小说交到他手里时暂被定名为《爱空想的自负者》(The Romantic Egotist)。在帕金斯的帮助下,作者对小说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帕金斯又做了大量工作,出版社才予以接受(此外出版社无一人看中这部书)。帕金斯发现了新一代的文学天才。后来帕金斯又给作者的另一部长篇《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提出过很有价值的批评意见。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的出版赢得了批评界的一致好评,批评家门肯认为这部小说是他当时读到的“最优秀的美国小说”。这部书销量惊人,两年里印了十二次,近五万册。据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教授、菲茨杰拉德研究专家约瑟夫·布鲁科里(Matthew Joseph Bruccoli,193l一2008)的说法,只有当时普林斯顿的校长对小说颇有些微辞,他从教育家的角度观察,不能想象我们的年轻人大学四年里只是“生活在乡村俱乐部里”,不能想象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在自私打算和自命不凡的风气里度过的”。
书的出版改变了菲茨杰拉德的人生,毁婚的恋人赛尔达回来了,并且与他结婚,他和他的妻子成了“爵士时代”(他创造的术语)的“吉祥物”,他英俊潇洒,言词妙趣横生;他的妻子美丽动人,衣着入时。他们的生活简直就是一个不散的盛大聚会。在第一部小说出版以后的二十年间,他又写了《美与孽》(The Beautiful and Damned,1922),《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1934),《末代大亨的情缘》(The Love of The Last Tycoon,1941)四个长篇。人们一致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最优秀的小说,也是我们中国读者最熟悉的美国小说之一,作家在书中用讽刺和同情的笔触描绘了一个“美国梦”的破灭,这部书也成了他的代表作。菲茨杰拉德潜心创作长篇小说,但只有第一部小说给他带来巨大收入,因此,为了支撑婚后奢华生活的巨大开支以及妻子的医疗费用(赛尔达一九三六年精神分裂症发作),他也和当时的其他作家一样,靠写短篇小说来弥补不足。他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例如,《爵士时代的故事》(Tales of the Jazz Age,1922),收集包括《五一节》(May Day)和《一颗像里兹饭店那么大的钻石》(The Diamond as Big as the Bitz)等十一个短篇小说,以及《所有那些忧伤的年轻人》(All the Sad Young Men,1926),收集包括《冬天的梦》(Winter Dreams)和《赦免》(Absolutionr)等九个短篇。菲茨杰拉德的第四部长篇出版后评论界反应并不热烈,作家自己也很苦恼。同时又为了应付经济上的困难,他到好莱坞电影制片厂改编电影剧本,并动手写他的最后一部长篇《末代大亨的情缘》。菲茨杰拉德从大学时代起就酗酒(尤其爱喝伏特加),又有年轻时留下的肺结核病根,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最终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生前并没有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在他去世后,由比他高一届的大学时期的好友、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编辑出版。在菲茨杰拉德去世后,他的作品又不断出版,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纪,他的作品仍在赢得读者。
二
菲茨杰拉德第一部小说的出版,使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二十年代,他几次前往欧洲,例如,法国的巴黎和里维埃拉避暑胜地,在那里结识了旅法美国文化人,尤其是与海明威交往甚深。所以有人说《人间天堂》写的是大学里的“迷惘的一代”,但是,这部小说的意义并非只局限于大学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