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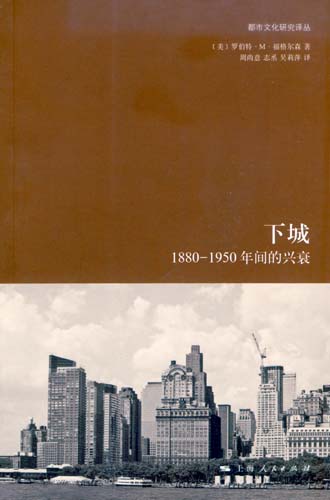 因《革命之路》而“复活”的理查德·耶茨,在他的《复活节游行》里完全暴露了自己悲剧主义的人生观。小说开头的第一句,“格兰姆斯家的两姐妹都不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回过头看,总是让人觉得问题始自她们父母的离婚”,好像危言一般,给初读者的心头投下一片阴霾。 因《革命之路》而“复活”的理查德·耶茨,在他的《复活节游行》里完全暴露了自己悲剧主义的人生观。小说开头的第一句,“格兰姆斯家的两姐妹都不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回过头看,总是让人觉得问题始自她们父母的离婚”,好像危言一般,给初读者的心头投下一片阴霾。
耶茨成长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时的美国人活得并不洒脱:禁酒,种族隔阂,连离婚都是一种被人诟病的家丑。耶茨眼中的世界基本上也是晦暗的,甚至在写作时,他也经常习惯性地让角色嗜烟嗜酒,让他们变得和自己一样。和《革命之路》一样,《复活节游行》又讲述了一个女性渐渐在现实中失去光彩的故事。
格兰姆斯的家庭很普通,母亲曾想在房地产业干番事业,很快败下阵来,父亲则优柔寡断,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两人最终离婚了。这场破灭的婚姻间接影响了二女儿,也是小说主人公爱米莉的反叛。
爱米莉的姐姐,格兰姆斯家的长女萨拉早早嫁掉,搬到长岛北部的庄园去了。爱米莉留了下来,老老实实读大学,在那里接受了女性解放的理念。随后的40年的成人生命中,她身体力行,竭力不受婚姻的束缚,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反讽,最终,爱米莉恰恰得靠那些离她忽近忽远、随时发生关系并随时可能断交的男人来定义自己,性解放导致了自我的虚无,两性关系的反叛者,反而被自己孤立在外。
除了人的命运,小说中还有一些准确的象征——映衬着爱米莉无趣人生的城市风貌,那种典型下城和西区白人的公寓生活。小说详细叙述了格兰姆斯一家的搬迁史,起初离开纽约,来到新泽西州的郊区特纳弗莱,后来回到纽约郊外的拉什蒙特。搬迁的轨迹显现了这家人的经济状况发生着变化,而回到纽约郊外的拉什蒙特,回到纽约下城,则意味着他们无可奈何的经济状况。
根据罗伯特·福格尔森在《下城——1880~1950年的兴衰》中所述,美国大城市的下城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独特的景观,从19世纪下半叶起,美国大城市开始形成商务区集中、住宅区分布于外围的格局。只是很快大萧条就降临了,下城遭到致命的冲击,大批商铺关门,写字楼空置,地价下跌,美国中产阶级大举向外围商务区迁移,最后彻底搬到了郊外。
爱米莉和母亲回到纽约下城,渐渐暗成纽约下城的白人孑遗,有钱人把家越搬越远,没钱人为节约交通成本,捧牢在写字楼里的饭碗,而别无选择地留下:现在他们要适应与种族上或民族上的少数群体混居了。在这里,这个商务区,她体验了两次堕胎,换了数不清的不靠谱的男人,在婚姻自由和性自由方面,她沿着父母开辟的道路愈行愈远。就这样,看着一个本该有着美好前途的年轻女孩一步步陷落于全世界的希望之都曼哈顿,此时再归咎于父母婚变,或责怪妇女解放运动的简陋荒唐,都不怎么合适了。
在我眼里,爱米莉的遭遇已真正变成了一个关于下城的寓言。约翰·厄普代克擅写美国中高档次的中产阶级的堕落,他们以“正统”美国人自居,拿着一笔丰厚的遗产饱食终日,当政府的应声虫;而理查德·耶茨则补上了地图的另一块,即二战结束以后,下层中产阶级的孤独无依。
任何一个现代都市社会,在贫富悬殊拉大的情况下,都可能出现这种“下城”式的孤独:在中低收入人群里,幼儿失养,老无所依,青壮年人因为背负了沉重的经济收入而活得了无尊严,而地方政府与则一味地帮助高收入人群去实现他们美好生活的理想。城市在郊区化的过程中,由于资源流向和政策倾向的单一,而把民间社会生生撕成两半。到六十年代初,选择住在纽约下城公寓里的人分享着同样的景观,同样的心情:孤独——这一耶茨小说的最大母题,不仅是心理的,而且是社会意义上的。爱米莉这位“自由女性”的晚境越发凄凉,童年和姐姐参加复活节游行的场景,成了她最后的美好回忆。复活节是让人思考死和再生的日子,然而“复活节游行”这个题目却只是指向一帧伪欢快的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