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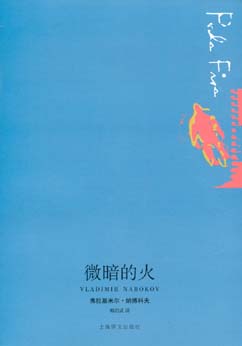 有一则传闻,纳博科夫成名作《洛丽塔》涉嫌剽窃,至少灵感嫁接自他人。纳博科夫在籍籍无名的年头里,偶得一本有关恋童癖的小说,当时只是读读罢了,没刻意往心里去,到面对打字机盘算着写个什么书稿时,这故事便浮出记忆,顿时非同一般。并传《绝望》是他对早年不光彩行为的公开忏悔,《微暗的火》中也留下了蛛丝马迹。有鼻子有眼。 有一则传闻,纳博科夫成名作《洛丽塔》涉嫌剽窃,至少灵感嫁接自他人。纳博科夫在籍籍无名的年头里,偶得一本有关恋童癖的小说,当时只是读读罢了,没刻意往心里去,到面对打字机盘算着写个什么书稿时,这故事便浮出记忆,顿时非同一般。并传《绝望》是他对早年不光彩行为的公开忏悔,《微暗的火》中也留下了蛛丝马迹。有鼻子有眼。
有了这个八卦做底子,三月里读书就平添了一星半点微妙的侦探味,可谓文本外的乐趣,意外所得,随书附赠品。小道消息的生命力或价值何在,这应是其中之一。珠圆玉润不着痕迹如纳博科夫,读他的作品还真应从外找个有争议甚至子虚乌有的线索突破,要真的找不着头绪,自造一个未尝不可,尽管往往要背上误读的恶名。据说,纳氏喜欢读侦探小说,我的解读方法可算歪打正着。
纳博科夫最妙的侦探体小说当数《眼睛》。用“侦探体”来定义,是指在这部小长篇中可发现最平庸的侦探小说最惯用的手段,偷情,暴力,自杀,争风吃醋,跟踪偷窥,不一而足。男的高鼻梁,面色苍白的高贵。女的金色卷发,挂一双肉嘟嘟的腮帮子。神似的是整本书简直是浸在酒水里,映着交错的觥筹,凌乱的人影。人皆是有闲有产者,这跟一般的侦探小说别无二致,想一想,发生在无产者阶层里的侦探故事多么缺乏美感,缺少娱乐精神,也无法满足种种人性特点。
三分之二的篇幅有足够的理由验证纳氏是侦探小说行当的新手,细节暗示,悬念设置,节奏掌控,都很到位,泄露他身份的是其出色的语言能力,很少有侦探小说作者语感这般出众,他们个个急不可耐,拖着情节撒开双腿向前跑,很少注意跑步的节奏和音色。纳博科夫不然,他边跑边侧耳倾听脚下响动,难免步履迟滞。《透明》里,纳氏写了一个类似的人物,休·伯森。此君重身姿轻成绩,打网球很见水准,不逊专业人士,却未赢过一场比赛,他要求完美的平衡击球姿势,在现代竞技中等于弃械投诚。
文学顽童纳博科夫,一生都在大声嚷嚷着,“狼来了!”,如狼真的现身,那就不是文学,也非纳博科夫。读者若在《眼睛》中看到一个阿加莎·克里斯蒂式或约瑟芬·铁伊式的收尾,这部小说不过是无数不出奇的侦探小说习作之一。小说的归宿本可朝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和胡安·鲁尔福的方位走,荒诞、魔幻、传奇,或鬼话连篇。纳氏迥异,现实中略带冷酷,以不乏诗意的手段,撕烂善意的可能性。拿一般定义上的侦探小说审度这个结局,它无疑很不专业。倘若侦探小说最终诉求是真相,《眼睛》要比多数侦探作品更专业,什么比近乎粗暴地展示人的处境更为真实?
原计划介绍纳氏四本书,实际上重点仅在最精致单薄的《眼睛》,当然也提及《透明》,一个跟书名完全颠倒的故事,但就其整体气质,又非常吻合“透明”二字,像瑞士松林中的一颗琥珀,缩小并保存了那个动人的年代,借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灵感,我称它“沉默的证人”。(当然,这是一本不错的作品。)小说天生就是证人,高下在于其是否诚实,需注意,摄影式写作恰与诚实背道而驰。纳氏作品的情节,我不想多交代,纳博科夫并不耽于虚构故事,但他的故事结构却不马虎,若拎起一根线头,我将遏制不住来个彻头彻尾的文本分析,把线团层层剥离。
到底纳氏剽窃的传言是真是假?我们似乎并未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也无法求解,如有人要牵强附会地举证《微暗的火》、《绝望》是纳氏的自我拯救,那么,《魔法师》又作何解?一位中年男人迷上一个踩着旱冰鞋的十二岁的小姑娘的故事。纳氏称它为《洛丽塔》的“轻微脉动”,灵感产生自报纸上一则猴子画画的新闻,这无聊新闻与畸恋有什么牵连?让人相当费解,但我相信这一说法胜过剽窃事件。道不清来龙去脉才是文学,倘若拿了鸡蛋孵出小鸡,这是普通的生物学现象。如何平衡说得与说不得,是纳氏作品与侦探小说最大区别,而非桥段的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