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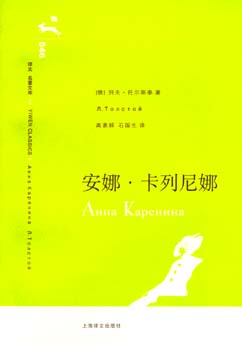 工业革命之后,火车、铁路、车站可以说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新生事物之一。有许许多多伟人、凡人、甚至文学人物的故事和命运与这几个互为一体的新生事物联结在了一起。 工业革命之后,火车、铁路、车站可以说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新生事物之一。有许许多多伟人、凡人、甚至文学人物的故事和命运与这几个互为一体的新生事物联结在了一起。
一
2007年9月初的一个夜晚,在莫斯科的列宁格勒火车站,我准备乘车前往彼得堡。进入车站大楼后,我很快就联想到,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写到的那个彼得堡火车站就是这里。先是在候车大厅,然后是在车站里面的月台上,我一边漫步,一边试图从那陌生而神秘的空气中嗅到安娜·卡列尼娜和伏伦斯基曾经呼吸过的气息,试图从月台和月台下面的铁路上的某个陈旧的缝隙里感受到他们在此相遇时的踪迹。然而,不仅季节与这对情侣相遇时的季节对不上号,就是时代也已经远不是小说所描写的19世纪70年代。车站大厅里散发着浓烈的汗味,月台上吹拂着九月份舒适的暖风,丝毫没有安娜·卡列尼娜初到莫斯科时那种寒冷的雾气,也没有安娜离开莫斯科时那种漫天飞舞的大风雪。但是,尽管岁月走过了一个多世纪,这座现实中的火车站可能经历过多次修建,小说中写的决定安娜·卡列尼娜命运的那条铁路线肯定没有改变,她初到莫斯科时呼吸寒冷空气、与伏伦斯基发生那冥冥中决定他们后来命运的互相一瞥的地方也肯定就是这里。
当晚十点多钟,开往彼得堡的列车开动了。我躺在硬卧车厢的铺位上,听着车轮有节奏的连绵向前的哐当声,心里禁不住依然思绪起伏,浮想联翩,满脑子都是安娜·卡列尼娜与车站、火车、铁路密不可分的故事。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安娜的真正显身是乘坐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火车,安娜与冥冥中的冤家伏伦斯基相遇、安娜最后的卧轨自杀也是在莫斯科的火车站——现在是列宁格勒火车站,小说里是彼得堡火车站。心潮澎湃的思绪很快把我带到小说中描写安娜在莫斯科与伏伦斯基相遇后、乘火车返回彼得堡的那个部分,那个预示着安娜必将陷入后来把她连生命都焚毁了的爱情的部分。当时,安娜已经在莫斯科那个场面宏大的舞会上点燃了伏伦斯基的激情,伴着车窗外面呼啸的大风雪,她在昏暗的车厢里一边读一本英国小说,一边反复重温在莫斯科的经历。想到那场舞会,想到伏伦斯基的身影和面孔,她情绪越来越有点神经质,精神恍惚,甚至感到某种恐惧。小说里写到:“她觉得她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手指和脚趾都在痉挛,喉咙里有样东西哽住,喘不过气来……”甚至有一阵,她感觉到自己在往下沉,自己却不仅不觉得可怕,而是很有趣。随后,在中途一个车站,她冒着暴风雪到站台上呼吸清冽的空气,试图驱散一下一路上攫住她的心魂的那种躁动;这时,她又遇到了特意追随而来的伏伦斯基,又看到或自以为看到了伏伦斯基脸上和眼里那种让她怦然心动的又恭敬又狂喜的表情。在呼呼叫的风雪中,伏伦斯基直截了当地表白了对她的控制不住的爱慕,说出了她内心渴望、理智上又害怕的话。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地开始了。
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火车路程约七个半小时。一路上,我辗转反侧,回想着从小说里读过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爱情,思索着列夫·托尔斯泰登峰造极的小说艺术,和他从《安娜·卡列尼娜》开始、作为一个伟大的宗教与社会思想家所做的苦苦探求。的确,在世界文学史以至文化史上,托尔斯泰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文学巨匠和文化高峰。他的思考和感受,曾被认为是代表着19世纪世界的良心;在某种意义上,他在今天依然代表着人类的良心。如果要列举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位最伟大的作家,我想争议最少的就是托尔斯泰。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曾经对比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认为巴尔扎克的文学成就根本没法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见《驳圣伯夫》),他说:“巴尔扎克给人伟大的印象,托尔斯泰身上一切自然而然地更加伟大,就像大象的排泄物比山羊的多得多一样。”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几年做的统计,托尔斯泰的小说是除了《圣经》之外,最受读者欢迎的世界经典名著。要是向文学爱好者做一个“你心目中的世界十大文学名著”问卷调查,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读者会想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即便你尚未阅读过这些作品,你也一定耳闻过它们如雷贯耳的名声,或是从影视中看过安娜的爱情故事、聂赫留朵夫的灵魂忏悔;因为只要谈到世界文学,你就无法越过它们。
二
英国作家毛姆在《巨匠与杰作》一书中曾经把《战争与和平》列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但是,在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作品中,最受世界读者和专业人士推崇的可能要数《安娜·卡列尼娜》。这倒不是因为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婚外情故事,满足了很多普通读者的好奇心理;而是因为托尔斯泰在叙事上所达到的雍容大度、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在刻画安娜作为一个女性追求自由爱情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时所达到的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的真实高度,在展示列文作为作家本人的影子进行精神探索时所传达的剔除虚伪的复杂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