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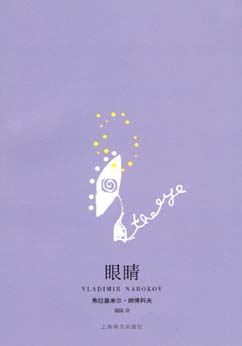 纳博科夫的文学动机向来孩童般单纯,除玩乐之外别无所骛。然而在智力和感觉的敏锐度上,他又是一个阅书无数、功力深厚的老江湖。两相结合,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可视作高级的精神游戏。这本仅仅80页的《眼睛》中,纳博科夫把人类最古老的谜题——灵魂,塑成一个魔方,弄乱,交给读者,“用一位英国老太太,两名研究生,一位冰球教练,一位医生,一位邻居的十二岁的孩子做试验”。结果,那位玩心未泯的孩子最快找到了答案。 纳博科夫的文学动机向来孩童般单纯,除玩乐之外别无所骛。然而在智力和感觉的敏锐度上,他又是一个阅书无数、功力深厚的老江湖。两相结合,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可视作高级的精神游戏。这本仅仅80页的《眼睛》中,纳博科夫把人类最古老的谜题——灵魂,塑成一个魔方,弄乱,交给读者,“用一位英国老太太,两名研究生,一位冰球教练,一位医生,一位邻居的十二岁的孩子做试验”。结果,那位玩心未泯的孩子最快找到了答案。
小说的主人公斯穆罗夫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旅居德国的”,“年轻”、“潦倒”的“俄国知识分子”。批评家们如果点击这些标签各自的超链接,所能获得的知识足以摆平大多数二、三流小说,可幸《眼睛》一定不在其列。斯穆罗夫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阶级、性别或时代的必然产物——纳博科夫对“必然”避之不及:“那个穿维多利亚时代格子布裤子的刻薄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资本论》这失眠和偏头痛的成果的作者所做的努力,纯属徒劳。”斯穆罗夫像神灯传说里那个被魔法师选中的少年阿拉丁,兀自在书页间经历命运的波折,好让那些脑力过剩、夜不能寐的读者疲惫满足、安然入睡。
斯穆罗夫和有夫之妇玛蒂尔达的关系被其丈夫发现,遭到一顿羞辱和毒打。斯穆罗夫绝望之下回到家中开枪自杀,却给救活。本来就喜欢“睁大眼睛”“审视自己”的斯穆罗夫,被那一枪打得灵魂出了窍:“自从那一枪……之后,我一直怀着好奇而不是同情观察自己,而我痛苦的过去……现在我已觉得事不关己。”“至于自己嘛,我是一个旁观者。”
出窍的斯穆罗夫就这样时不时散发出加缪《局外人》的味道。这种旁观状态在加缪那儿是探讨存在意义的切入点,在纳博科夫这里却是拿来游戏的好道具。可怜的斯穆罗夫像空中的一只眼睛一样,看着病愈的自己在书店找了一份工作,通过书店老板结识了一户俄国贵族,成为他们家的座上客,并一厢情愿喜欢上这家的年轻小姐万尼亚。那个更加可怜的斯穆罗夫却还不知道自己的灵魂已经独立出去,兀自纠结于自己的心病,在万尼亚的圈子里丢尽颜面。
“眼睛”对斯穆罗夫好奇心盛,不时也有偏爱和怜悯。强烈的好奇心推动情节进展,让小说成为一个“追寻斯穆罗夫”的侦探故事。“眼睛”想要借助周围人对斯穆罗夫的印象还原一个斯穆罗夫的本相。为此,它甚至曾经“附到”斯穆罗夫身上,抢劫了一位朋友的日记。然而为了让他人眼中斯穆罗夫的形象更加准确,它又不得不全面了解他人的生活。正如要看清灯光下的事物,必须得熟悉“一切因灵魂而异的灯光效果”。而他人生活的灯光,又正是“眼睛”自己。
加缪只顾冷冷地旁观“自己”,《眼睛》却要旁观自己、旁观别人、旁观别人眼中的自己、自己眼中的别人……旁观不够,还要带入感情,要为爱情心潮起伏,让事态愈加复杂。好在纳博科夫为人厚道,如估计到阅读有难度,多在前言里提示一番,以免读者一头雾水,批评家误入歧途:“可怜的斯穆罗夫的存在只取决于他在别人头脑里的反映,而他们的头脑接着也像他的一样,被置于同样离其的镜子私的窘境中。”
结尾,“眼睛”和斯穆罗夫两片分裂的灵魂终于合而为一,为希望的一缕幻影放手一搏。斯穆罗夫一如既往地败退,但对“眼睛”而言,“他们的整个存在只不过是银幕上的一片微光”。“观察从人的一生中的一个灰色、贫瘠、单调的瞬间怎样发生在现实中开不了花的神奇而美好的事件,其中自有一番痒抓抓的乐趣。”——眼睛的乐趣,蝴蝶爱好者纳博科夫的乐趣,读者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