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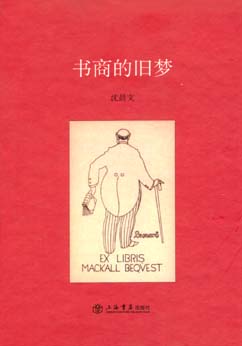 下午买到《书商的旧梦》,晚上一翻就是一整夜。在偏晚的凌晨,我在书的扉页上写完名字和日子之后,又加上了这样一句话:“连夜读完,希望沈先生长寿。这一辈人,等到老年才有机会吐露真扉,也可叹。”(沈先生编书过千,然真正出版著作,直到2003年,时年72岁)然后,把书合上,放在下午刚邮购来的一叠《炎黄春秋》之上。 下午买到《书商的旧梦》,晚上一翻就是一整夜。在偏晚的凌晨,我在书的扉页上写完名字和日子之后,又加上了这样一句话:“连夜读完,希望沈先生长寿。这一辈人,等到老年才有机会吐露真扉,也可叹。”(沈先生编书过千,然真正出版著作,直到2003年,时年72岁)然后,把书合上,放在下午刚邮购来的一叠《炎黄春秋》之上。
之前一直在犹豫,究竟有没有必要为大众读者推荐沈昌文的文字。上次的《阁楼人语》是如此,这次刚买到《书商的旧梦》,也是如此。在对他诸多称谓中,出版家是头一位的(但他干脆自称“书商”,连“出版人”这样的词汇也少见),曾主政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多年的他,乃奔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来以来的文化热潮中最前沿的幕后操盘手,无论是《第三次浪潮》、房龙著作新版、《情爱论》、文化生活译丛这些曾引领一时风尚的文本,还是《读书无禁区》和《人的太阳照常升起》这些惊雷雄文,背后都有他。
即便如此,可没心没肺的读者,总容易不以为然地丢句话出来:是又如何?都老黄历了。再说,我直接读书就完了,又何必知道这是谁编的,谁出的?
我所忌惮的,也正是这个。
而沈先生的《人民有读书的自由》一文,也以“记得《读书》杂志,不必记得沈昌文之流”开篇。看到这篇文章,不由得想起我在一篇《阅读,既是赏花也是吃草》的文章结尾:“读什么不读什么,是比说什么不说什么更重要的权利。”仔细想来,我这句延续着“读书无禁区”思路的话,固然没有问题,但究竟还是狭隘。有什么样的出版社编辑和负责人,实际上决定着我们阅读权的落实和行使!这就值得有点脑子的读书人去了解,去琢磨。
在《罪孽之一》中,沈先生在谈到当年《宽容》中一处如今已被恢复的删节及《情爱论》中被删掉的“情色话语”等地方后,发出了如此感慨:“编书五十余年,经常自己称道和被人称道的种种‘功绩’。但是想想这类胆大妄为的删节,大概我辈要忏悔的地方更多。”尽管,他在前面的《第一本历史教科书》一文中已经道出了“如果照印不误……我的饭碗肯定要丢了”的隐情。除了有陈原这等老前辈给的“底气”外,这个从1957年后,心里总是想着以“稳”为上,少做惊天动地的傻事的人,在办杂志时,已经悟到要学做“淘气孩子”了,比如他无意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有不少谈“性”的言论,甚至很开放。而中国早期的开明知识分子,也都关心过这问题,有不少论著和译作,后来就推出了《情爱论》、《性心理学》和《重审风月鉴》等轰动一时的书。
可按沈先生晚年的思路,光“淘气”还不够。他在书中,对两位女性的评价甚高,一个是因酷爱读书最后毛遂自荐成为《读书》编辑的赵雅丽,也就是名震古诗文研究界的“扬之水”;另一个则是他少年就认识的旅美女作家於梨华。对于后者,他从其对她父亲有褒有贬的评价及得罪台湾当局被列入黑名单等事迹,给出了“从来就是一个倔强性格”的评语。对前者,不仅大面积引用张中行对她的好评,更是以《脑后那根反骨》为题,认为大家乐于谈其人其事,乃是因为她的那根“反骨”,所以她能在流行“读书无用论”的“文革”中耐下心来读书,能在经济拮据时节衣缩食买书,也能在“商潮”盛行时依然做些与书有关的寒酸工作。
扬之水因爱书,成为优秀编辑,终成出众的学者,这是书痴的理想路线之一。沈先生在谈及《愤怒书尘》的作者,出版人、法兰克福书展前主席卫浩世时说,凡书业中有成就的人士,大多经历过一番思想乃至行为骚动的历程。他们不安于社会上现成的摆布,于是向书这个最敏感、最“触及灵魂”的行业进军,通过书来述说自己的人生诉求。如果多一些,长着“反骨”的“书痴”,成为中流砥柱,沦陷于娱乐时代,“病在谋略太多,机心太重,理想太少”的中国出版界,面貌得以改观的可能性定会大一些。
且不必说到思想史和传播史此般宏大的话题上去,说点小功效也好,我是边看边留意里面谈到的书,然后顺藤摸瓜,在网上搜购,我统计全书举荐的书约32种,我已有8种,其他感兴趣的十几种,都淘得七七八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