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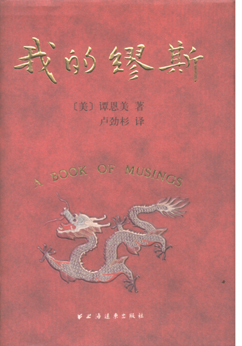 此书是我对生命的沉思冥想,其中包括我在8岁时用到的种种比喻,比如我把书籍比作一扇扇打开的窗户,照亮我的房问;也包括我在为母亲写祭文时的想法,我试图总结她的一生,还有她给我的生活以及写作带来的影响。 此书是我对生命的沉思冥想,其中包括我在8岁时用到的种种比喻,比如我把书籍比作一扇扇打开的窗户,照亮我的房问;也包括我在为母亲写祭文时的想法,我试图总结她的一生,还有她给我的生活以及写作带来的影响。
我用“缪斯”为散文集命名,因为其中多数篇章是偶得之笔,并非正式的论述。文集中收录的有些是我在各大学府演讲时的讲稿,篇幅较长;另一些篇幅短小,特别是那些在几近绝望的时刻完成的短文,比如为追忆我的编辑、超凡脱俗的费思·塞尔而写的一篇颂词;再比如一次劫后余生,我发给朋友们的电子邮件,那次险些让我丧生的意外还上了全国新闻;书里还收录了一首我写给丈夫的情诗,虽只寥寥数语,但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却是最严格的一次历练。
我收录了一些比较长的文章,比如其中一篇写到电影《喜福会》制作过程中的感悟和体会。当时一位记者发来传真,提出若干问题,我一股脑儿把想到的都写出来作为答复。结尾时,还不知道下一步将发生什么。在注释中,我对后来发生的事进行了后续说明。文集中还收录了1990年我到中国探亲期间的部分日记,那次旅途让我享尽天伦之乐,不得不把平日里典型的美国作风抛到一边。希望这篇文章能博读者一笑,也希望读者能借此了解我在生活中多么执著于观察。通过观察,我生活中的每件事情皆有可能转变成影像或者问题,如果幸运,还可能激发出创作灵感,虽然事情本身可能微不足道。本书的最后一篇是最近才完成的,原因出于命定,但也揭示出希望。
文集中很多文章的缘起说来惭愧。《母语》那一篇写在一次学术座谈会的前夜,仓促而就。那次会议讨论的命题是“语言的状态”,与会的诸位学者在这一领域都比我博学。这篇发言在《三便士评论》(The Three Penny Review)上刊发,之后又人选(1991年美国最佳论述选集》(The Best American Essays,1991)。我因此怀疑,是不是所有创作都该在凌晨2点钟进行,且一定被逼得焦头烂额才好。《母语》还被选为“爱普”(Advanced Placement)和“赛达”(SAT)的英文项目考题,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让《母语》的作者受宠若惊,因为当年在“赛达”的语言项目考试中,她的得分只有400多。写作是组织安排文字的艺术,如此糟糕的成绩使她认为,以写作谋生于她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至少在1969年时是没有可能的。
在文集的收集整理期间,我产生了一个新体悟。这种体悟如此明显,让我惊讶的是,此前我竟然一直都没有意识到。我的所有创作,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也无论是直抒胸臆或是间接说明,我所探寻的始终都是命运,以及在宿命之外的诸多选择。在书中各篇关于命运的沉思冥想中,我发现我已经表达了自己的个性和逐步形成的生命哲学,这些都传达了我独特的声音。以此为据,我在创作时选择了想讲述的故事、人物,还有相关的细节。在我的小说中,我所塑造的人物,在他生命的各个时刻,特别是遭遇变故时,总是会追问自己究竟该相信什么。虽然我从没想过要通过这部文集对自己的小说进行解读,事实却达成了这样的效果。
因此,虽然这些文章的写作出于不同目的,总体上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某些想法、人物以及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转折时刻不时地出现在此书中。这些无意为之或者有幸想到的缪斯,再次显现出我对宿命和宿命之外的各种人生选择的痴迷:诸如抉择、机会、幸运、信仰、宽恕、遗忘、表达的自由、对于快乐的渴求、爱的抚慰、坚定的态度、坚强的意志、接踵而来的好运气、恪守传统、安抚人心的祷告、渴望奇迹、期盼别人伸出援助之手、陌生人或所爱之人的慷慨给予。
我以为,总体而言,改变命运的因素是希望。希望始终存在,它会让所有的事情变得可行。母亲是希望最坚定的捍卫者,她教我认识到命运的种种面貌。如果说命运是时钟的分针,没头没脑地向前走,母亲总能找到办法让它倒转,她总是这样做。比如她曾经固执地认为我长大以后会成为一名医生,之后又向所有愿意听她唠叨的人夸耀:“我一直都知道,总有一天她会成为一名作家。”命运就凭借这种说法发生了改变,希望也因此成真。现在我是一位作家,像她所预言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