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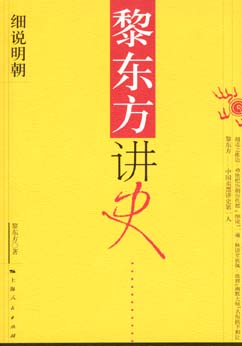 黎东方教授,旅美著名历史学家,师从国学大师梁启超和法国史学大师马第埃。曾先后在中外多所大学任教。在英国牛津大学讲学时,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抗战时期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卖票讲史,引起轰动,其盛况,决不亚于今天的“百家讲坛”。之后,他以讲史的形式,写成了《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三国》《细说民国》,创造了被称为“细说体”的写史新体裁。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了“黎东方讲史”系列,现摘编其中精彩片段,以飨读者。 黎东方教授,旅美著名历史学家,师从国学大师梁启超和法国史学大师马第埃。曾先后在中外多所大学任教。在英国牛津大学讲学时,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抗战时期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卖票讲史,引起轰动,其盛况,决不亚于今天的“百家讲坛”。之后,他以讲史的形式,写成了《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三国》《细说民国》,创造了被称为“细说体”的写史新体裁。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了“黎东方讲史”系列,现摘编其中精彩片段,以飨读者。
明太祖
创造明朝的,是朱元璋,朱元璋最初“反元”,毫无自创朝代的雄心,只是迫于环境而不得不投身于一个“反元复宋”的武装团体而已。
帮助朱元璋取天下的,武人多而文人少。文人除了李善长以外,数得上的只有刘基、宋濂。刘基(伯温)的大名,到今天仍是差不多家喻户晓的。这大概是由于大家相信他是“烧饼歌”的著者。乩坛上,也常有他降临题诗。
他反对朱元璋用他自己的朋友杨宪,说杨宪不能“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反对用汪广洋,说汪广洋气量褊浅,更甚于杨宪,反对用胡惟庸,说胡惟庸好比是一匹劣马,必定把车子拉垮。
朱元璋不完全听他的话。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三人朱元璋都重用了。
胡惟庸毒死刘基,是在洪武八年。刘基原已于受封为“诚意伯”之后,在洪武四年三月告老还乡,在青田的山中饮酒下棋。若干时日以后,胡惟庸告他因为“谈洋”地方的风水有王气,和当地的老百姓争墓地,朱元璋生了气,取消他的诚意伯俸禄。他来到京师(南京)谢罪,留居京师以明心迹,生了病,胡惟庸在洪武八年元旦带了医生来看他。他喝了这医生的药,觉得肚里总是有一块拳头大的东西,再度回乡,挨到四五月间去世。
胡惟庸被杀,是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杀得一点儿也不冤枉。此人既非功臣,而且谋反有据。
皇帝朱元璋觉得他比谁都好。他不像李善长那么老朽,刘基那么古怪,宋濂那么迂腐,杨宪那么量小,汪广洋那么荒唐;相反,他善体人意,又很谨慎小心:既“曲”且“谨”。
他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深得这“一人”的宠信,为所欲为,作威作福,并且可以大大地捞下去,聚满了各方送来的“金帛、名马、玩好”,还能有什么不满足的?然而,他竟然不满足,硬想取朱元璋而代之。为什么?
最大的原因,是“心里不太平”。俗语说:爬得高,跌得重。他深知朱元璋最恨贪污,倘若有一天他的贪污的事被朱元璋知道,如何收场?况且,毒死刘基的事虽则是天知地知他自己知,也难免没有一天,天网恢恢。(依现存史料而论,刘基之被胡惟庸毒死,不像是朱元璋授意。)
自从胡惟庸的案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了以后,洪武十三年以前上下一心,共创新局面的风气,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大臣的是“伴君如伴虎”,当小臣与老百姓的是“虎口余生”,朱元璋自己是虎了,却也未尝不是厕身于极多的其他老虎之中,“骑虎难下”,以虎骑虎。他竟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与江山,还算是他能干,至于因此而博得了“雄猜”、“滥杀”、“刻薄寡恩”、“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富贵”等等,千古的恶名,他也只好认了。
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去世。马皇后之死,对他是情感上与事业上的一大打击。从此,他缺乏了一个可以无话不谈,而且够资格对他婉转劝谏的人。马皇后不仅在当年是他的红颜知己,而且一生信佛,慈悲为怀,惟恐朱元璋待部下不够宽厚。(有一件小事,最足以说明马皇后的心好。她视察了国子监,便建议不仅学生们应该有公费,他们的家眷也应该由政府予以赡养。)
马皇后既死,朱元璋之所以决意不再立后,不是没有原因。
明成祖
成祖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之中,算是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一个。
他有统驭的能力,然而私心过于公心。他在当皇帝的二十二个年头之中,把中国的境内治得相当太平,这是他的功。
把宦官重用了,使得明朝从此变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这是他的罪,他的最大的罪。其次,杀方孝孺、铁铉、齐泰、黄子澄等人,株连极多,而且也杀了已经投降的李景隆、盛庸、耿炳文之流,残忍两个字他是逃不了的。忠于他的文臣,如蹇义、解缙、杨士奇、夏原吉、李时勉,都曾经被他任意抓了放在监狱,关了或多或少的时间。他之看不起读书人,尤甚于乃父朱元璋。
我们进一步批评他,他的若干武功,在事实上多半是不必要的穷兵黩武,而且并无实效。对北元与瓦剌的征讨,次数虽多,而没有一次捉得住敌人(阿鲁台与马哈木)。实际上他自己放弃了大宁三卫的领土,使得辽东与察南接不上气,自找麻烦,贻患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