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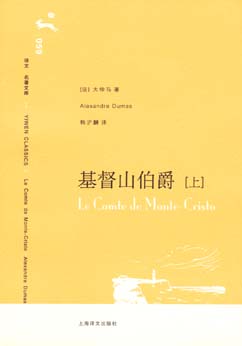 《基督山伯爵》——有些译本又译作《基督山伯爵恩仇录》,后面这个名字比较有民国时期的风味——总之这本书坊间版本很杂,有书脊包金,明晃晃的豪华精装本,足以用作杀人武器;有多卷本,封面硬邦邦的,放在书架上像是一排砖头;还有缩写版的口袋书本。电影的版本也堪称花里胡哨:德帕迪约的大鼻子伯爵版,美国的马戏团伯爵版,直到2002年又拍了一出英语版的《新基督山伯爵》。 《基督山伯爵》——有些译本又译作《基督山伯爵恩仇录》,后面这个名字比较有民国时期的风味——总之这本书坊间版本很杂,有书脊包金,明晃晃的豪华精装本,足以用作杀人武器;有多卷本,封面硬邦邦的,放在书架上像是一排砖头;还有缩写版的口袋书本。电影的版本也堪称花里胡哨:德帕迪约的大鼻子伯爵版,美国的马戏团伯爵版,直到2002年又拍了一出英语版的《新基督山伯爵》。
复仇的题材总是吸引读者,尤其中间又掺杂着财宝、爱情、阴谋还有无数奢华的景观,这本小说里有法国上流社会最高规格的社交活动,又有天方夜谭式的东方派头,绅士间的决斗,异地的狂欢,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本热闹有趣的小说。
许多年前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生涩,总觉得里面的贵族都是些怪里怪气的家伙,说着听不懂的话,像在打哑谜。唯一读得高兴的地方是伯爵在小岛上发现宝藏那段,金锭也好,宝石也好,和想像中的财宝情景一般无二,另外舞刀弄剑的情节也不错。
从前看这本书看到的是复仇,再大一些又看到了报答、宽恕、信仰,最初读到结尾的“等待和希望”时毫无所获,总觉得伯爵的一切都不是靠等待得来的,记得美国片《沉睡者》里,那个童年惨遭侵害的检察官每晚入睡前都要读一遍《基督山伯爵》,以巩固自己的复仇之心。而复仇,恐怕是除了生存之外,最能够支撑人的动力,不然巴勒斯坦的人弹何以会前赴后继?
最近再读,注意力却不知不觉转移到了其它地方。
《基督山伯爵》在复仇故事之外,更像一本十九世纪法国贵族的年鉴。
对于贵族的最初印象,来自一些老式黑白电影,他们无论男女都有又卷又长的假发,夸张可笑的眼影,还有浑身的蕾丝边,男人的绑腿上紧紧地扎着袜带,女人一刻不停摇着羽毛扇子。总之,像一群活动的布偶。
再后来知道了“三代出一个贵族”这种说法。说明贵族这东西和贵重商品不太一样,有钱还不行,要又钱又有时间,前两代还不能断掉,不然充其量也就是出一个地主老财的土鳖儿子。
《基督山伯爵》里的贵族形象,无疑都是些活物,同时又修正了三代出贵族的说法,阿尔贝子爵的贵族派头又大又正,不过是个二世祖;伯爵本人的风范更是把眼睛长脑瓜顶上的巴黎人吓了一大跳,却是泥腿子进城,头一遭。贵族之形之神在整部小说里都活灵活现。阿尔贝(我很喜欢这个角色)被意大利强盗绑票后,假如等到天亮还没有赎金送来,就要脑袋搬家,这时候他还能倒头呼呼大睡(真的睡着了,不是装的),除了对朋友的一份信心,还有心底的一股子傲气。维尔福的老诺瓦蒂埃老爹杀掉告密者,虽然是预设的阴谋,但是手法却堂堂正正,丝毫也没有小家子气的狡诈气息。
小说里的贵族都是些斯文有礼的家伙,但外出溜达的时候眼光总是盯在别人美丽的女眷身上,罪恶感是断不会有的。狂欢好似没个尽头,真有尽头的话,或许是战场上的一颗射来子弹,一柄砍来的马刀,更多情况下,这子弹和刀剑来自决斗场。安享荣华整日里懒洋洋的贵族和人拼起命来,也和街上的混混儿一样,好似活得根本没有明天。不同的是,混混儿多半是为了保命而活而搏,贵族们要保的,只是名誉而已。眼睁睁看对手举起枪对准自己脑袋而不能动,底线在此。
难怪有那么多人为贵族着迷,《刀锋》里的艾略特不辞辛苦去巴结那些破落贵族的后代,只是为了一窥当年他们祖先在金锦原上的神采,而这神采早已经随岁月消散无踪,他们的子嗣们成了巴结在有钱人周围的一群苍蝇。
《巴法利夫人》中,爱玛迷恋的贵族则既阴沉又狂放,带着点粗野的气息,对于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来说,光是那些华美的小客厅,还有里面那些派头十足的男女就足以让人满足了。《项链》里的玛蒂尔德对于贵族的梦想就要具体许多了,她幻想里的粉红色的鲈鱼还有松鸡翅膀,以及那些白色的幔帐,不消说肯定出自流行小说。
现在的人们厌烦了“小资”“中产”,开始对“贵族”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对于一切手到擒来司空见惯的东西来说,已经消逝的事物肯定吸引力更大些。如同早先的罗马人,后来的巴黎人,以及再后来的美国人还有后续的一切暴发户,什么都见过了什么也都经历过了,那么未曾经历的便弥足珍贵。所以“贵族”又成了新流行,许多有钱人期望通过像培养孩子打高尔夫球这样的举动训练出家族里的贵族品种——其实还不如看看《基督山伯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