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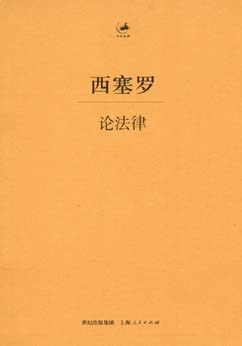 只有少数人才能服从理性的指引,才能遵循自然的法则,多数人则容易屈从于恶习和谬见。 只有少数人才能服从理性的指引,才能遵循自然的法则,多数人则容易屈从于恶习和谬见。
HBO2005年度史诗巨作《罗马》(ROME)中刻画了这样一位西塞罗:一位自负的虚伪贵族;一位饶舌的平庸政客。在元老贵族面前他义正言辞地要捍卫共和国的自由、贵族的荣耀,阿莱西亚战役之后却带头投降凯撒;在庞贝的军营外他声称渴望回到家乡过和平的田园生活;战争结束之后他却又返回罗马投入元老院无休的争吵之中。
这一戏谑的形象对于西塞罗而言也许不甚公允,但却也反映出传统思想史界对于西塞罗的典型评价:作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罗马的后继者,他既无创造力亦无感召力;他涉猎了广博的希腊思想,却很肤浅;他的学说是折衷主义的,而且缺乏一致性和深度。因而,西塞罗除了他的修辞术外,其余的全部学说不外是为他人做嫁衣而已:作为一位著名的希腊罗马思想的传递者。
然而,即便我们承认上述的评价带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性,在思想史中,西塞罗仍然是一位无法避开的人物。他也许不是一位好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位深邃的哲学家,但他仍然称得上是一位勇敢的政治实践者。与他所敬仰的希腊先贤相比,他所要面对的是与希腊城邦政治迥然有异,而且情况更为错综复杂的罗马社会:三巨头联盟的瓦解,元老院的软弱,凯撒与庞贝的明争暗斗。在这种局势之下,在讲求实际的罗马人那里,美丽的神话已经激发不了热情,唯有荣耀的历史才具有说服力。因此雄辩的政治演说辞不能再寄希望于哲人王的理想国,柏拉图在叙拉古可耻的失败足以让罗马人对这些说教嗤之以鼻。作为罗马人的西塞罗,既要调和这种希腊哲学与罗马实践之间的断裂,又要处理自身思想中的矛盾。也许正是因为此,在《论法律》中西塞罗处处声称自己为怀疑论者,怀疑绝对知识的可能性;也许正是因为此,《论法律》与《论共和国》一样,采取了对话体的形式,“隐藏自己的观点”,陈述相互冲突的论点,寻求最有可能的答案。
作为《论共和国》的续篇,《论法律》在前篇回答了什么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之后,着重于为这样一种政治制度描绘出一副法制的框架。面对当时已然腐败堕落的共和国,经历过从“国父”到被放逐者之惨痛巨变的西塞罗不得不借他人之口表达了这样的无奈:最智慧的东西可能既是人类智慧难以达到的,也对人类生活没有意义;因此理论上更高的东西可能不得不随时让位于必要的东西,让位于民众迫切关心的东西。此时,我们就不能认为西塞罗不过是一位希望恢复古老共和国制度的理想主义者。事实上与他的精神导师一样,西塞罗相信王制才是最好的,却也是最不可能持久的。因而书中的对话者们口中古老的罗马共和历史并不存在于真正的历史中,而是部分虚构的历史。西塞罗用这种迎合罗马人口味的方式叙说了另一个贴近现实的理念,一种确保贵族制的混合政体。这也许不是最好的政体,但却是政治实践中所能达到的最好形式。
然而西塞罗怀疑这种政体能否完全依赖自然的偶然、历史的运气,因此这一混合政体必须体现某种“法治”特征,将智慧者的智慧植入国家的法度之中,确保后继者不能背叛,这就是《论法律》的主要任务。为此,法与其为之服务的政体之间就必须具有某种一致性。因而,西塞罗认为法的本质与国家存在的基础相一致,即正义。在这里西塞罗重述了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理念,传自古希腊却又不断流变的自然法思想。在柏拉图那里神圣的自然法指引我们的理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性寻找自然法,而在斯多葛派观念中,真正的法便是符合自然的正当理性。这是普遍适用、永恒不变的法则,想要改变这种法律便是犯罪,违背这些命令便是放弃人本性中最美好的东西。
但是,很难相信西塞罗本人是这种严格的斯多葛教义的完全信奉者,这便是《论法律》中西塞罗思想的不一致性。因为虽然他相信国家与法律都需要这种严格的正义原则,但是残酷的历史已经让他接受了柏拉图晚年的结论,先不要追问正义为何,正义的代价过于高昂,完全正义的制度在人间大概是不可能的。这样,西塞罗一方面认为必须解释正义的本性,而且必须在人的本性中寻找;但另一方面又承认为了实施统治的法律,必须接受习俗和历史流传下来的“罗马法”。
人本性中所独具的正义便是理性,人被理性所指引,必能达于美德:这就是最高的法的原则。然而这只能是部分正确的,考虑到《论法律》所面对的读者——体面而高尚的人,不能相信这些难以证实的基本原则会得到承认。因而,西塞罗期望能够让他们相信所有正当而高尚的事物都是由于它们自身的缘故而被渴求,相信没有任何东西将被视为好东西,除非其本身就值得赞美。如此一来,西塞罗就为他的斯多葛原则加上了限制条件,他不能相信严格的正义原则能够和公民社会和谐共存。只有少数人才能服从理性的指引,才能遵循自然的法则,多数人则容易屈从于恶习和谬见。崇高的自然法便这样让位于智慧者的法律,这种法律将只根据恰当使用财产的能力来分配财产权。这便是低标准的自然法,智慧者的法律,虽然不是最完满的,却能为人民——特别是那些体面而高尚的人——所理解和遵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