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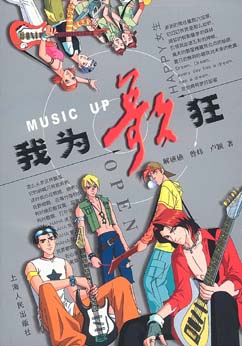 图书炒作像打开了书业的潘多拉盒子,给书业带来转机、热闹和竞争的同时,也带来了虚浮、无序和恶性膨胀。 图书炒作像打开了书业的潘多拉盒子,给书业带来转机、热闹和竞争的同时,也带来了虚浮、无序和恶性膨胀。
2005年4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经过近半年的酝酿,推出了作家曹文轩的长篇小说《天瓢》。这一次推《天瓢》,“金丽红、黎波、安波舜”金三角仍然沿用了以往的畅销书操作模式——“选题策划、编辑制作、印刷设计、宣传推广”环环紧扣,抓住4月最佳市场启动期,借媒体的炒作,将图书推向市场。
自17年前运作第一本畅销书——王朔的《过把瘾就死》到今年的《天瓢》,出自金丽红、黎波之手的图书,本本成为畅销书,“金黎模式”一时成为出版界寻求自身突破的借鉴模式。对于出版者而言,环节中的前三者是图书出版的普遍流程,而宣传炒作在当前的出版现状中就显得重要起来。最初的模仿来自那些机制灵活、运作周期短的图书工作室,自2000年以来,北京各大出版社也发现了畅销书给出版社带来的渠道资源,纷纷组建营销宣传中心,大张旗鼓地做起了图书宣传炒作。
前两年郭敬明的《幻城》的炒作经费已创下了出版界图书炒作费用的新高,然而巨大的宣传炒作也为出版社托起了一个畅销书作家,整合了发行渠道。2004年的畅销书《那小子真帅》可谓图书工作室与出版社联合炒作的成功个案,仅与网站合作的宣传经费也达到了几十万元。《爱的语法》则将炒作由报纸、网站等成本较少的媒体转到了电视广告上,并起用了明星代言人张娜拉,其背后的费用已经突破了百万之巨,此举将2004年的图书炒作之风推向了顶峰。
然而,图书的炒作到底带给出版社(出版商)、图书市场、读者乃至文学创作界哪些影响?大多数出版社之所以对书进行炒作,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媒体提高出版社自身的社会认可度,更多的则是借助畅销书疏通发行渠道,建立出版社的公信力。
春风文艺出版社借助郭敬明的一系列图书疏通整合了出版社的发行渠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借助《哈利·波特》系列图书重新梳理了发行渠道,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我为歌狂》也为其带来了更多的经销商。所以,对出版社而言,针对重点图书的宣传炒作并不仅仅在于取得单本畅销书的利润,而更多着眼于拓展销售渠道,树立出版社在读者、经销商心中的口碑,从而争取更多一线作者,使出版社在长远发展上获利。然而,宣传炒作的所有费用必然以成本的方式进入图书定价,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图书价格虚高不下的原因。
而对于出版社的从业人员而言,“金黎组合”的畅销书制作模式并不具备可复制性,出版社内部生产图书的四个环节都是各自割裂的,很难做到环环相扣。宣传炒作已经成为图书编辑的一项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编辑对图书自身质量的把握,来自编辑层面的浮躁之气必然会对书的质量产生影响。
对于图书市场而言,书业的炒作之风呈现了一种虚假繁荣的表象。然而市场真的繁荣吗?从出版数据上看,2004年,全国出版的图书近20万种,如何在如此多的新书品种中选择重点,上架推广,对于新华书店等经销商而言,可以依靠的主要资讯就是媒体的推介和图书的内容。好酒也怕巷子深已经成为出版业内不争的事实。
对于有宣传炒作的图书,书店会积极上架推广。然而,很多从未在媒体上露面的普通图书也许还未曾打开包装就进入了书店的库房。据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我国图书的库存已经超过了300亿元。图书各个层面的炒作已经成为影响书店正常销售的因素。
当然,图书的炒作之风直接吹到的还是买书人(读者)。图书炒作的形成是出版者和媒体的“共谋”,然而,没有买书人的积极参与,料想再有规模的炒作也不会产生效果。难怪圈内的文化记者也无不唏嘘:“现在的读者是最容易被误导的。”读者承接着炒作的结果,也承受着虚高的图书价格。这无论对于图书大市场还是读者都不是良性发展的态势。
业内人士,也包括很多读者,对于媒体上的书评书讯,往往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不是收了红包,拿人钱财替人说话,这些被讽刺为“红包书评”、“红包书讯”的内容一时间充斥了部分媒体之中,可见低俗的炒作之风侵害着媒体的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