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以后的杭州日臻繁荣,主要原因在于海上贸易的开辟、城市民生用水问题的解决、长期生活安定,特别是到了北宋时期,周边地区海岸石塘的修筑、城区运河的整治、乡村水利的兴建以及西湖风景名胜的播扬,都较好地抬升了杭州的社会文化地位。在明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发展较诸中国其他地域具有明显的先进性,而杭州城作为东南大都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又常常引起时人与后世人们更多的怀想。下文选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贤亮所著《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插图修订本)》,邀读者穿越到明清时的杭州,一睹其繁华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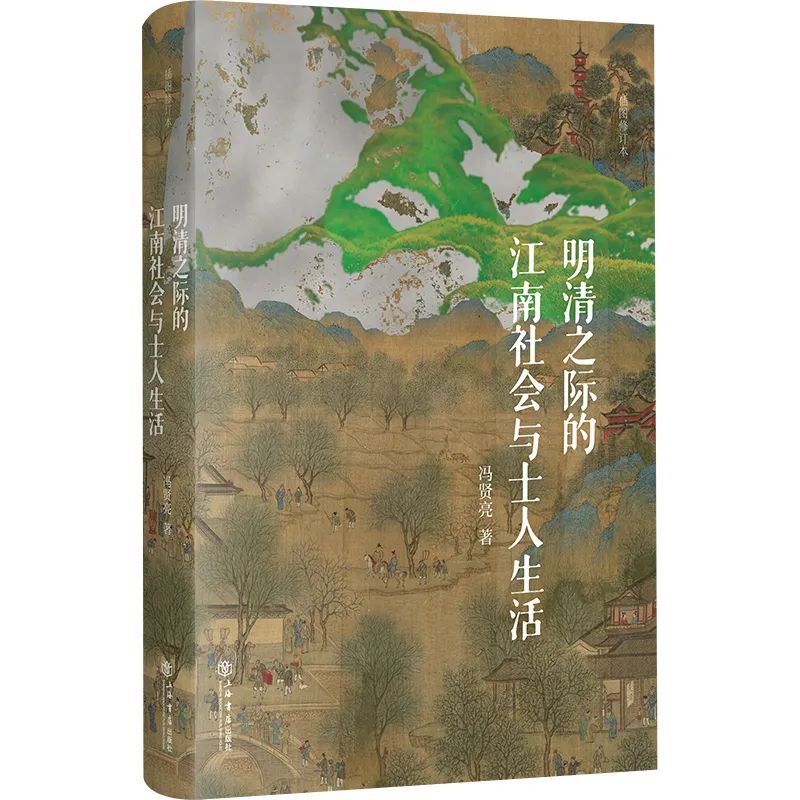
《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插图修订本)》
冯贤亮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明代的杭州,经济生活繁华。这种繁盛,宋代已经展现,时人称这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1] 经历元末的社会动荡后,杭州与其他地方一样,经济复苏,社会稳定,商业繁荣。一些传统的手工业生产,特别是丝织业与船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虽然明朝初期的杭州,还远不如南宋时代的繁华,但到万历年间,原先是所谓的“草深尺余”、孤逸为群”的近郊僻地,也已“居民栉比,鸡犬相闻,极为繁庶”。[2]
至于从唐宋以来城市中早已存在各色各样的休闲娱乐,如杂剧、蹴球、讲史、相扑等,一直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每逢节庆,更是热闹非凡。城市生活区中那些堪称休闲娱乐的中心,存在着许多比较固定的表演场所,叫做“瓦子”或“瓦舍”,供给各式说唱、杂技团体表演,常常吸引大量的市民前来观赏。类似这样的休闲表达形式,在江南地区,已不局限于城市,而是遍及整个城镇乡村,乡村搬演杂剧等娱乐活动更是经常性的事情。
作为浙江的首善之区,杭州城里百货所聚,当然包括省内各府县的各种特产:“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磁,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3] 生活景象自然繁华,即使在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4],呈现出十分富丽而诱人的图景。
在这样的环境中,必须有一定的谋生依赖,适应城市生活的压力,否则很难生存。王士性曾说:“身不有技则口不餬,足不出外则技不售。……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5] 这类人群,依靠一定的技术,也能达到生活上的小康,甚至发家致富。姚旅在《露书》中,除士、农、工、商及兵、僧外,还列出道家、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弈师、驵侩、驾长、舁人、篦头、修脚、修养、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十八民,都是所谓不稼不穑者,职业分化堪称细致。[6] 在明代仍占有重要地位的杭州出版业,书坊都有敏锐的市场意识和经营策略,都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重视通俗文学、科考用书和实用类图书的刊刻出版,而且注意图书的传承价值,有利于文化积累,所以既能迎合市民阶层的喜好,也普遍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7]
为了谋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很多人需要依靠精湛的生产技术,由此也使地方上的整体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从而闻名全国。[8] 在多样化的经济生活之繁荣的前提下,人们的生活需求日趋多样,奢化的生活风习不断兴起,各类娱乐活中心及其服务行业,甚至是青楼,都极兴隆。这种情况在有关江南的文献中,记载甚多。元末明初传说中的江南巨富沈万三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成了后世人们的榜样,世人争以求富为务,生活饰物更是争奇斗巧。[9]
归有光曾指出,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生活环境,对于孕育地方富户,其实十分重要。在明代洪熙至弘治年间,六七十年间,国家已进入了所谓“休明之运”,“天下承平,累世熙洽”。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乡村民众力于本业的生活,十分有利,“安其里居,富其生殖”的生活状态完全是可期的。[10]
官至吏部尚书的仁和人张瀚,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其祖上“以酚酒为业”,后以纺织谋利,“家业大饶”。[11] 张瀚又言及一些家族的兴衰,皆因生活奢化所致,因其亲历,感觉十分真切:[12]
世远者吾不知已,余所闻先达高风如沈亚卿省斋、钱都宪江楼,皆身殁未几,故庐已属他姓。至如近者一二巨姓,虽位臻崇秩,后人踵事奢华,增搆室宇园亭,穷极壮丽;今其第宅,皆新主矣。此余所目睹,安有如江楼、省斋者。
|